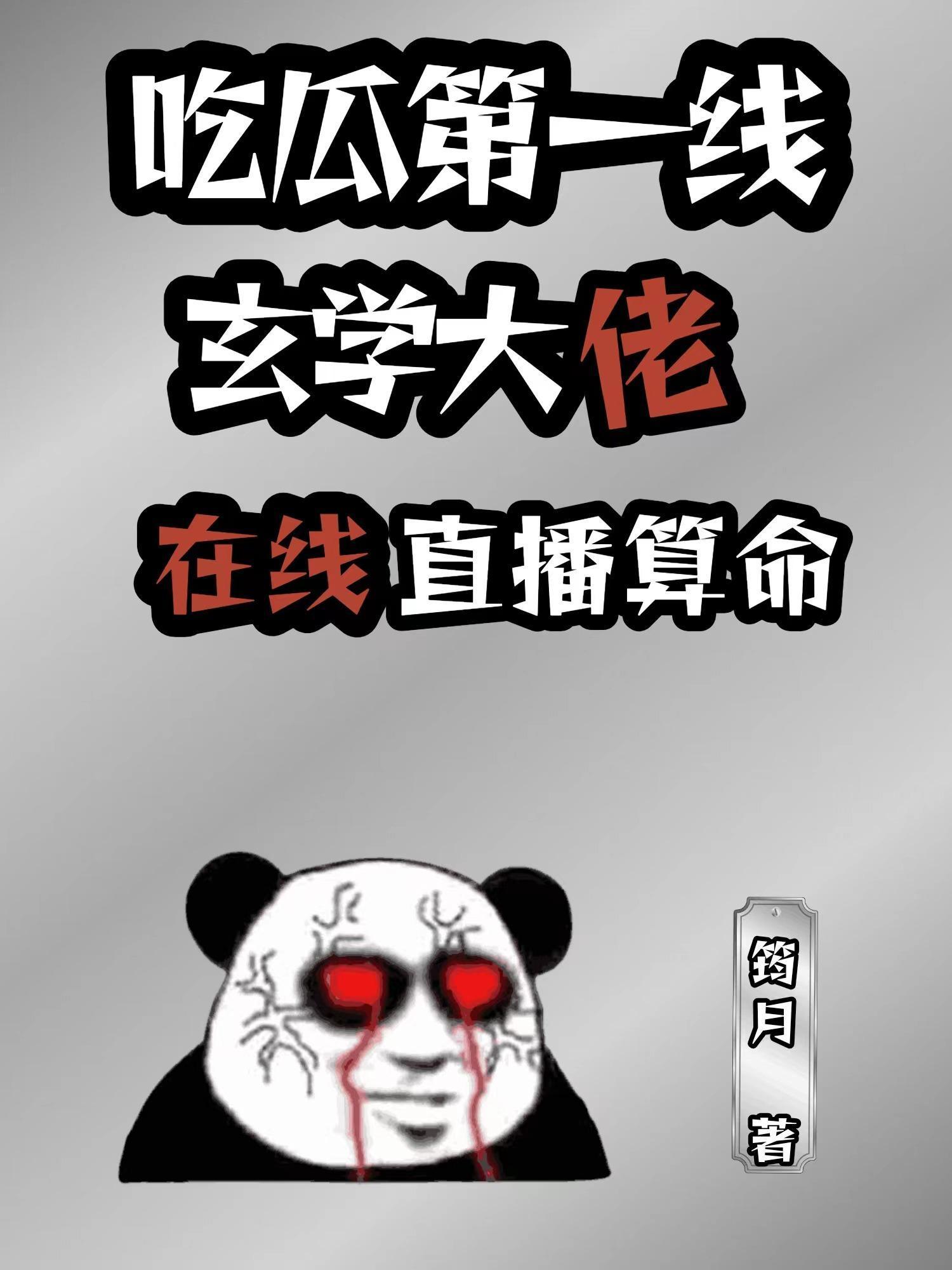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电影意志的考验 > 历史精神的不坏肉身(第2页)
历史精神的不坏肉身(第2页)
>
《马路天使》(1937)
美国的研究者认为《马路天使》受到弗兰克·鲍沙其(FrankBe)的影响,他拍过一部同名电影StreetAngel,这部影片似乎在1928年的上海公映过。但我看赵丹的回忆录,他记录了此片生产的过程,它取材于他们几个人一起出入下等小酒馆的经历,袁牧之导演将这些经历写成了剧本,它仍然属于原创。它可能部分地借鉴了StreetAngel的运镜方式和人物关系,一样是底层民众的联合——流浪艺人和准妓女等身份者具有天然亲近感,而底层男女的恋爱成功,往往有阶级结盟的意味。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影人并未盲目排斥美国电影,反而发现了美国电影中颇为亲切的底层表述,StreetAngel即为一例,但中美“左倾”
色彩的电影又绝不相同。
《马路天使》必定以悲剧收尾,这是重要的区别。StreetAngel是“happyending”
,这意味着在现存社会中仍具有获得出路的可能。中国左翼电影要否定
这个可能,暗示阶级矛盾已难以调和了——做妓女的小云死去,无产阶级朋友们默默聚集,一筹莫展,电影至此结束。重看左翼电影,多是毁灭性结局,除非他们决定前往一个新的空间,往往是参加抗战。而抗战的所在地是晦涩的远方,与延安有隐约的关系,但又不是特别清晰——毕竟那是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公映电影。失败性结局的无可避免,暗示这一体制的失败,也暗暗为革命寻求合法性。
十年后上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结尾一样是毁灭性的——儿媳投江自尽,老妪恸哭于江边。这场放映在列治文市的昆特兰理工大学进行,观众以华裔长者居多。观片前,有一位老人向我回忆本片的结尾,吴茵坐在水边大哭的那场戏,她说:“我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幕。”
此片一般不被划归左翼电影的谱系,左翼电影是一专有名词,一般以1937年为终点。抗战爆发后左翼影人星散各方,袁牧之去延安,蔡楚生远避香港,拍摄了两部抗日影片。香港沦陷后,蔡楚生又被迫逃亡,历经柳州、桂林,沿途看见百姓刍狗般的命运,自己也差点丧命。他在1944年底到达重庆时,“除了手里的两本《辞源》外,一无所有”
。这和剧中男主角的命运相差无多。因为有这般经验,所以这部电影元气饱满,虽长达三个小时,叙事上仍有从容不
迫的气质。
蔡楚生又有很好的古汉语修养,所谓一江春水向东流,片中频繁出现江水和月亮的镜头,这些事物国外也有,而作为意象,它们在中国文化里代表了更广泛的意义。当战乱来临,母亲为儿子做衣服,临行密密缝,这番情景国人更能领会。本片完成后连映三个月,所以后来的史官评价本片时,认为它很好地“配合了”
当时的政治斗争。所以它虽不属于“左翼电影”
这一概念范畴,但以政治光谱而言,又属于左翼电影。
本片有两条主线——妻子在上海、丈夫在重庆,两条线索向前并行推进,终于交织在一起,男主角的三个女人同时居住在一个屋檐下,原配正在做另两位情妇的用人!在张爱玲编剧的电影里,用人往往是不老实的,早期影片的用人也不被赋予天然的道德优势,而左派电影里的用人多淳朴良善,如果不是作为潜在的革命者存在,至少是作为一种控诉性的力量,《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如此设定的。
本片其实一直存在着第三条线索,男主角的弟弟在上海郊区抗日,女主角跳江前让儿子以后向叔叔学习,这个叔叔如同左翼电影中的进步青年一样,语焉不详,仿佛还有隐秘的身份。爱国主义、抗日成为左翼表达的重要掩体,它隐约有所暗示却又不明言,而观众已经可以领会,知道此处不是归宿,彼处才有大
光明。从1932年起被明确的左翼叙事规则,越接近于胜利在望,越强调矛盾的不可调和,它从相对温和走到极端冲突和必须摊牌的地步。而之后左翼成为官方,那不再是某一类影片的内在结构,而是所有影片的结构。
哪怕在“十七年”
(1949—1966)的古装片《刘三姐》和唯一用外国人做主角的影片《白求恩大夫》中,这一结构也稳稳地存在着。《刘三姐》里的主角来自两广民间传说,一说刘三姐是唐朝人,她喜欢唱歌,唱起来三昼夜不停,人类学家据此以为刘三姐原是女巫。电影将这个人物进行了转化,使她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觉悟。“不是仙家不是神,我是山中砍柴人,只因生来爱唱歌,四方漂流难安身。”
为何唱歌有如此之难?因为这山歌俨然成了自由言论的象征,山歌就非庙堂之歌,它代表了穷人的观点。
“心想唱歌就唱歌,心想打渔就下河”
“唱歌不怕头落地,阎王殿上唱三年”
,其中的人物自由、率直、神完气足,行动果敢勇猛,当然这是夺取政权之后安全状态下的叙事。此片有左翼电影一贯的劳动神圣理念,它对土地所有权持模糊的态度。莫管家不准刘三姐等人采茶,说“你头顶着莫家的天,脚踩着莫家的地!”
刘三姐回答他:“众人天,众人水来众人山,劈开荒山造茶林,哪有莫家一滴
汗。”
这显然强调劳动者的优先,似乎是用自然权利来对抗约定产权。
在更早的广西彩调剧里,劳动者并未反抗莫员外的土地所有权,只是他们要在莫员外土地上唱歌而不被允许,故而爆发冲突。影片的改编是契合马克思主义的——注重劳动的价值,认为土地等生产资料是资产者剥削的手段。无视对方的所有权而仍然采获其上所有,无疑已经具有暴烈的革命性,但是在1960年,这一点还不够,因为本片仅仅用唱歌反抗,所以《刘三姐》遭受“否定暴力革命”
的批评。
劳动自豪、农民智力优越,秀才则毫无知识分子风度,头脑粗蠢,且是有产者的帮凶。这里对知识者的嘲讽已经非常极端,有人认为这已经是“文革”
的前奏,虽然它拍成于1960年的10月。知识分子绝少成为中国电影正面的主角,《早春二月》(1963)几乎是唯一的,但是它被打成了毒草。《白求恩大夫》是1964年的电影,在温哥华放映这部影片是为表达中加友谊,但如那个时代的其他影片一样,概莫能外,其中也涉及同样的问题,且更为复杂。白求恩虽然是国际主义者,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但是他毕竟是科技知识分子,且来自北美的资本主义国家。
一部电影往往有戏剧冲突,不仅仅是电影吸引力的需要,冲突也是基本的社会事实,黑格
尔则从逻辑上论证了戏剧冲突的必然。毕业于耶鲁大学戏剧专业的张骏祥是如何在《白求恩大夫》里设计戏剧冲突的?他设计了一个国际主义者和地方之间的龃龉,尤其方大夫因为失误让士兵失去了一条腿,白求恩厌恶他并拒绝他进自己的培训班深造,但后来他了解到方大夫曾经是放牛娃,为了革命艰苦学医,他也了解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特殊性,于是忏悔了。中国左翼电影强调穷人的道义性,对知识者加以改造,但即使《白求恩大夫》这样一个讴歌外国人道主义者的影片里,同样包含着一个改造知识分子的内在结构,这是五十年后的我观影时所始料未及的。
三
从以上四部影片中发现同一个叙事结构并非难事,自20世纪30年代初到80年代初,历经五十年,这一结构从初建到成熟,最终固化,失去了开放性与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几乎难以从电影美学发展规律的角度去单独评价电影,美学自主领域的丧失如此彻底,是中国艺术史的悲痛,而仅就外在表征来看,旧结构决定和对应的美学范式潜力已耗尽,它们变得单调和绝对,丧失了视听吸引力。而新范式尚未建立,旧结构还在制约和塑造,不过是将正面转到了侧面罢了。罗愁绮恨的解决,都是要在旧框架中完成,换一个新的结构会使得账目混乱,失去了“复
仇”
的快感。
90%"
class="
bloter"
data-ckedit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