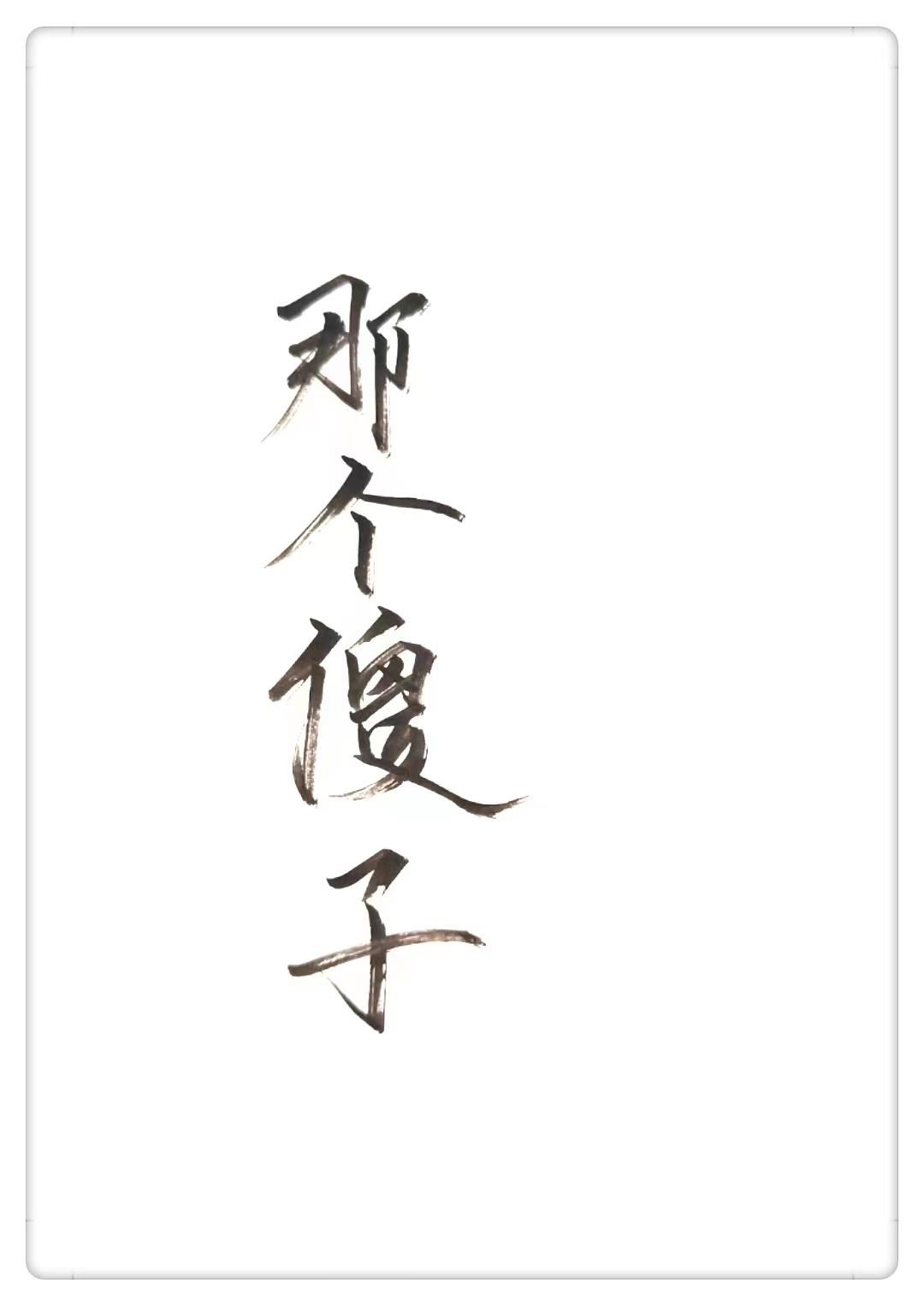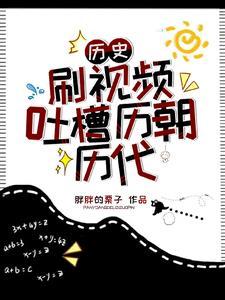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光明使者动画 > 他与她(第1页)
他与她(第1页)
有时,一些案犯有所顾忌,是不会在审讯室里全盘托出和一概吐露的,那种压迫感和氛围让人不安,许多零碎的记忆也难以回忆。
而在监室里,没有多余的旁观者,更重要的,他们可以否认说过的话。
“怎么就你一个?其他两个呢?”
任星凯对拘留所值卫警老马问道。
“闷得慌,而且那两个老烟枪了,不得要到外围解决。”
老马回答道。
“那正好,拿套装备给我吧。”
“你老是让我难办。”
“什么难办,办案!”
任星凯接过口嫌体正的老马递来的防护服,随即便穿着上了。
防护服由与看守所监牢同款特殊材料制成,非一般的能攻击无法击穿其防御,然而它只着重保护了要害的部位,原因无他,这新改进的一套仍将近十公斤,内巡警员就是穿着这样笨重的装备进行数小时的值守,直至换巡。
在这座冰冷的拘留所里,每名犯人无论罪名大小都被戴上了电子脚镣,关押在单独的监室内,在这里,监控的视线几近填满每个角落。
话虽如此,犯人在特定时间里依然是被允许外出到空地上放风的。
那时,他们的头上没有钢筋穹顶,一来是成本问题,二是取而代之了一条更为冰冷的规定。
一旦在押犯人被检测到以能升飞以越过外墙警示水平线的情况下,拘留所内外督警有权使用包括能在内的一切手段和措施将其捕回,且在此期间督警对出逃犯人的伤亡不负有任何责任。
当然,如果是个疯子,或是觉得自己足够强,强到能够从被挑选出来的二十名全副武装的能督警手中逃脱。
至于劳动、阅读或是其他娱乐活动,犯人之间也大都各自分隔,少有与他人交流的机会。
显然,能拘留所负有高昂的建造和管理成本,且其日常运行依旧困难,对于防不胜防的能犯罪者,根本没有完善的监管方法。
……
任星凯此行独自一人,他才出警回来,而身后还有数个案件等待自己处理。
“不会让你背锅的,老马,有事我担着。”
任星凯笑着说道,“又欠你一顿饭。”
“这都几顿了,我菜单都没见到过。”
老马回以一笑道。
“忙啊,不然折现算了?”
“得了吧,你还是赶快完事吧。”
说罢,老马便操作系统放任星凯通行了,他知道他有分寸。
实际上,警务人员应该持证件从安检通道识别通过,但那上面留下的记录无法修改,而便行道所采用的是不同的识别系统,可操作性上就大多了。外部监控当然拍到了任星凯,但若无事基本上没有人会去翻查录像。
任星凯先在监区二号楼见了一名刑犯,那儿的值警同样是他的熟人,只作了个登记的样子。
这般半私下的非正式问讯自然是不被允许的,只不过处处都要维护律法程序的尊严对案件的侦办而言往往使其费时耗力。
像任星凯常说的,不择手段和用尽一切手段是两码事,而且这也谈不上是什么手段。
在二层,任星凯停留在了廖光宇的监室前。
自从第三次心理治疗形式的问讯后,廖光宇已经两天拒绝出监室了,监控中,他整天就蜷坐在床角,不吃也不喝。
而明天,就是他上庭的日子。
此刻,系统上显示廖光宇所在的监室门打开了,不过那警员权当没有看见。
监室里,廖光宇依旧沉溺在空洞当中,不去想不去问,明明例行搜查和心理疏导昨天才进行过。
任星凯站在床边,他清楚廖光宇目前的精神状态并不乐观,在上次的讯问中,他暂时交还了廖光宇的手机,而后者现自己已经无法登录那款聊天软件了。
不止于此,廖光宇失去了所有与其联系的方式,而任星凯也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其人的信息……
“是我。”
任星凯摘下头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