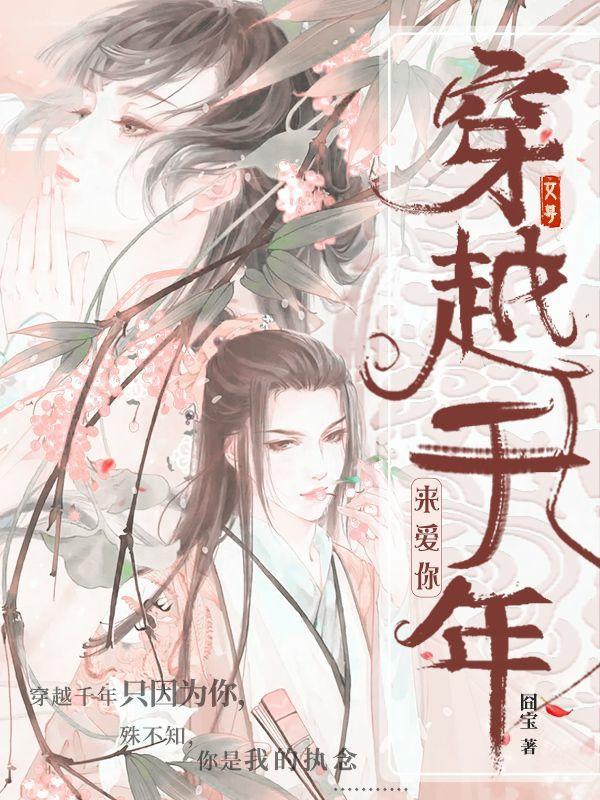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黎明之前番外路人甲 > 第93页(第2页)
第93页(第2页)
“等我们都二十一岁,就去领结婚证。”
她的眼睛闭得牢牢的,她听见自己从嗓子眼里轻轻地发了声回他。
“好。”
二十一岁结婚。
实现了吗?
谁能对十八岁的她说一声吗?
3
你看我啊。
劈开我的骨头,全是凌晨的眼睛,没有光,连黑暗都畏惧,也唾弃。
拆掉钢针后,血肉已愈合。那根食指有时小幅度地动过,但绝大多时候就这样,直挺挺的,弯曲不得。开始不适应,再渐渐去接受并习惯左手再也握不成完完全全的拳头。
戒指重新回到原处,刚好掩盖住疤痕。
公司租借的电瓶车很便宜,一百五一个月,但很脏,沙尘泥垢,把手也是脏黑的,伴着饭食馊臭味,反胃得他花了一个下午才清理好。
拆完恢复的第五天,便迫不及待地想骑车去送更多外卖,于是整理着着装,弯着腰在门口换着鞋子。
宋轻轻担心地看着他的手指,劝他能不能再缓几天去。他回头笑着说没大碍,不用担心,又用手臂勾住她的脖子,头低着,睫如黑鹅羽般,勾着嘴角,
说:“你就在家乖乖等我。我今天赚够了才回来。”
“可是你的手……”
“没事。”
眼里都闪着光。
背影在她无奈的眼里,由面到点,从点至无。
晚上的风如起舞的巨人,手脚像巴掌般扇在行人身上,沙粒的苦味被迫吞进喉咙里。他哼了曲欢快的调,又被风吸干。骑着电瓶车,穿行在宽敞无人的车道上,他回头看了看已经空空如也的箱子,胸腔里松了口气。
快到家了。
他又轻轻勾起嘴角。
今天干得不错,等会儿要去超市买点牛肉,买几个鸡蛋,还要买些什么……哦,对了,还有小朋友最爱的酸奶得给她买上,要放进肚腹间暖一下,省得太凉了对她的胃不好。
风声呼啸如鬼哭狼嚎,寒风像刀子凌迟着他的手背,灯暗成灰,风乱迷眼,他的眼眯成一条细线来抵御风沙的干扰。黑帽被他压得实实的,风却戏谑地一次次试图将它掀起。
起了又落,落了便起,像个弹簧。
左手时不时地脱离把手压着帽顶,似要压住所有苦难般用力而显得有些焦灼,一向平心的他终是忍不住暗骂一声。
这歪风。
似是听到他的骂声般,风进行了报复,用更用力的姿态发起进攻。
眼看帽子便要离开头发,他高抬起左手,一股刺眼的光却射进眼睛,要灼烧他……
他下意识地抬起手臂遮住光,惊慌在身体里汹涌澎湃,于是左手急忙放下,却因为食指的失力,左转力度不够而显得停滞。车子却以惊悚的速度奔来,一时,着急、紧张,各样情绪涌来,翻天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