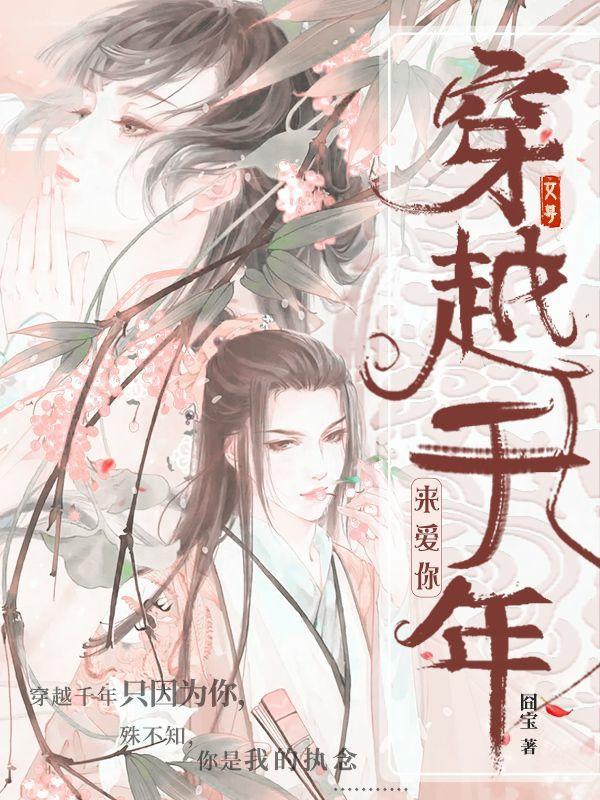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病弱alpha每天都在装病 > 第228章(第2页)
第228章(第2页)
玲儿看多了戏折子,坚信男人得了势,一定会抛弃糟糠之妻。 可是她们夫人不仅人长得漂亮,心地还善良。关景寻那不长眼的,要是连这么好的姑娘都辜负,真真该天打雷劈!
温宜见劝不动她,只能先领着人回府。玲儿骂了渣男一路,到家时温敏突然问了一句:“姨姨,渣男是什么意思?”
玲儿抱起跟着跑了一路的小敏儿,神秘兮兮道:“等渣男来了姨姨再跟你说,走,我们喂金鱼去。”
“好!”
最聒噪的两位离开了,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温宜有些恍惚,仿佛不久前的混乱都只是她的一场梦。
不,关景寻已经回来了。这是真真切切的。
尽管他们连最简单的交流都未曾有过。
温宜梦游般回了房间,拿出前一天未绣完的刺绣,坐在窗前接着绣起来。没绣几针便被针扎了手指,她一向仔细,做了这么多年女工,从未受过伤出过错。
温宜无措的站了起来,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恍惚至此。鲜红的血珠从指尖沁出,滴落在雪白的绣布上。
温宜这才察觉手指上的伤,正要放进嘴里,手却被人抓住了。
温热,潮湿。仿佛走了几万里的风,披星戴月。
粗糙的茧子磨在温宜的细滑手背上,一如苍老干裂的树皮,扎得她手疼。
温宜张皇的抬起头,尖叫声却哑在了嗓子里。
眼前的男人仍旧高大,却比四年前沧桑了许多。黝黑的面庞上,那双狭长的眼睛却要比四年前更加凌厉,只是静静地看着,便仿佛穿透了四年的光阴。
温宜愣愣的张开嘴,却不出一个音节。眼泪无声滑下,顺着脸颊滚落在那双粗糙的大手上。
男人慢慢抬起手,用手背在她的脸上轻轻擦了擦。
“瘦了。”
喑哑的嗓音仿佛几日几夜没有进水。
温宜眨了眨眼睛,薄薄的嘴唇嗫嚅着,却始终无法叫出那个名字。
直到被人搂进怀里,久别的胸膛还带着路上的风霜。
温宜嗅到了沙土的气味,喉咙一动,终于趴在人身上放声大哭起来。
男人轻轻拍打起她的后背,可以轻易张开弓箭的臂膀,此刻却轻柔的仿佛怕弄碎她一样。
温宜一直哭到眼睛都肿了,才擦着鼻子埋怨道:“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要进宫吗?”
“我看见你了。”
温宜仰起脸:“我知道呀,我看见了。我不要紧的,呜呜……”
“要紧,”
男人搂得更加用力,低着头在她耳边急切又克制的重复:“要紧的……”
温宜勉强止住的眼泪再次溢出:“圣上要是怪罪下来该怎么办?呜呜……”
“不会的,宜儿,你怪我吗?”
温宜哭着摇头,模糊的双眼已然看不清眼前的人。
关景寻帮她擦干净泪水,捧着她的脸道:“不能再哭了,宜儿,再哭眼睛就睁不开了。”
“我控制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