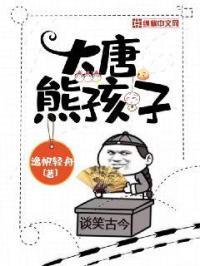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菩萨蛮朔风吹散三更雪 > 第1章 秋冬之交(第2页)
第1章 秋冬之交(第2页)
柳全摇头拒绝,二人拉扯一番,柳全腰上刀伤撕扯开来,他本就只草草包扎,现下整个腰腹都在阵阵痛,不觉间已额生虚汗。
柳全依旧嘴硬道:“没多远的路就到河庭城了,楚丫头你毕竟是千金之躯,万一到城门下让人看到你给我一个糟老汉赶车,岂不损了你的名声。”
楚轻影看出他脸色不好,将人推进车里,道:“都是些闲言碎语,只要不往心里去,影响不了什么,话又说回来,您怎么招惹的这帮银甲兵,还受了这么严重的伤?”
柳全半推半就地坐稳,解下罩在外面的棉服和外裳,身上的破旧香囊也沾了血渍,他扯下,往渗血的伤口上洒药粉,自嘲道:“别人不知道,楚丫头你也不知道吗,我可是叛军余孽,这些年为逃避朝廷追捕,四处躲藏已经习惯了,跟人起冲突,受点伤也是常有之事,不过我身子骨硬朗着,这点伤不碍事。”
马车辘辘朝前,傍晚的暖光从西天斜斜投来,给她利落的身姿镀上了一层金晖。
她沉静的面容已经洞悉到柳全的异样:“瞧这伙银甲兵的着装应是安京城的禁卫军,又人困马乏,想必赶了很久的路。全叔,您当年在军中并未担任要职,这都过去十年了,朝廷怕是早就忘了您这个所谓的叛军余孽了吧。况且您一直在北境活动,就算身份暴露,也该由现您的北境官员就地捉拿,如何犯得上安京的将军千里迢迢赶来。全叔,您同我说实话,您是不是惹了不该惹的人?”
柳全手上的动作停了下来,褐色的眸子深处有碎光闪烁:“你这丫头,不该打听的少打听,知道得越多,越危险,这话我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轻影反驳道:“对,您每次都打着为我好得名义,什么都瞒着我,就包括当年漠北一役到底生了什么,您也始终闭口不提,您”
“楚丫头。”
柳全打断他的话:“我渴了。”
轻影轻叹一声,将腰间的水壶扔给他,回头瞥见他充耳不闻的表情,不再逼问。
马车穿过迷蒙山涧,轧过斑驳的沙石路面,在红色云彩的掩映下悠悠驶向了河庭城的南门。南门守卫不多,进进出出的多是小商贩和平民百姓,马车混在其中异常扎眼。
轻影再度开口:“城中有我相熟的大夫,您先进城治伤。我也不敢保证那帮银甲兵不会追来,不过您放心,进了城我定会妥善安置您。”
“多谢楚丫头了,总算没白疼你这么多年啊。”
城门就在眼前,柳全如释重负。
他躬身从马车里迈出,然而,人还未落地,却忽闻身后传来甲胄碰撞之音,惊得他后背骤然一僵。
轻影扭身回头瞧了一眼,还是那队兵马,为的将领如隼的眸子正正盯着他们二人,奔腾之势如张开獠牙的洪水猛兽,仿佛下一秒便会将她和柳全给吞了。
轻影感觉大事不妙,眼见着城门就在不远处,她毫不犹豫地驱马狂奔而去。
守城的皆是楚家军麾下,着黑甲,不出意外,马车通过不会有人阻拦。
然而,就在黑甲兵让道放行的一瞬间,空中飞来一支冷箭,“咻”
的一声扎在了车辋前。
马车在城门前打了个急转,东倒西歪地停了下来。
“姑娘请留步。”
还是先前拦他们马车的将领,他这回带过来的银甲兵是先前的两倍之多,甫一至跟前就将二人包粽子般圈在了马车里。
天色已经暗下来,西天的余晖在黄土漫天的草坡上渐渐褪去光芒,人影在料峭北风中逐渐吹成了一道道细影。
观这帮远道而来的禁卫军阵仗,八成是盯上他们了。
轻影抬起乌黑的双目,一张白皙的脸在冷风中清冷而孤高:“将军是认不得这是谁家的马车?还是将军不知,西北侯就驻扎在这河庭城?”
将领道:“马车虽是侯府的,但马车里的人不见得,姑娘,您还是行个方便,让我们搜一下吧。”
轻影挑了挑眉,扬起随身佩戴的青黛剑,直指银甲兵。
剑尚未出鞘,单单是剑鞘的雕花便知是一把绝世好剑,加之轻影抬剑的动作熟练而利落,便可知她的身手不凡。
银甲兵也不是吃素的,旋即拔出手中长刀,刀刃在天光的折射下泛着锃亮的雪光。
柳全眸中微动,眼前的火药味太过浓烈,他艰难地挺直了脊背,按住轻影的手,挡在了她身前:“没事的,我下车让他们查一通又何妨,不必如此大动干戈,不必。”
话是如此说,但两边都不愿先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