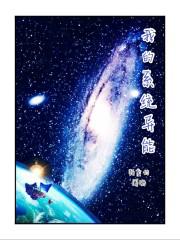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再嫁权臣望烟TXT > 第74章 你为了我好恨不得我死(第2页)
第74章 你为了我好恨不得我死(第2页)
朱玉笙早猜到朱维昌夫妇俩必定垂涎她带回来的东西,于是皮笑肉不笑道:“许久不曾出门,去街上转转。”
贾氏趁势跟着她进屋,利目一扫便见到依墙而摞的几口箱子,只是令人失望的是每口箱子上均挂着一把沉甸甸的黄铜大锁。
徐氏不放心,连忙跟了进来。
逼仄的房间,三个人转身都难。
朱玉笙假装对她的来意一无所知,径自就着早晨的残水洗手,余光扫见贾氏伸长脖子打量箱子的贪婪目光,心中暗哂。
她的亲生父亲朱维清持身清正从不贪财,谁知亲弟弟却活脱脱是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恨不得练成貔貅之能,只进不出。
贾氏一屁股坐在她床上,犹如回到自己屋子,热情招呼徐氏:“大嫂也来坐。自玉笙嫁出去之后,咱们娘俩还不曾见过面,不如坐下来好好聊聊。”
朱玉笙心中烦不胜烦,怀疑贾氏上辈子是卖狗皮膏药的,深谙粘上难撕的精髓:“二婶,我逛了一早上累了,想歇会。”
贾氏浑然不在意她赶客,见徐氏帮不上她的忙不说,见到女儿便眼圈一红,一副又要哭的模样,心中腻烦,索性道:“大嫂若是不舒服,不如回房去歇着?”
徐氏担了一肚子心事,一时怕贾氏欺负了朱玉笙,一时又怕朱玉笙不管不顾跟贾氏撕破脸,往后母女俩在朱家更难立足。
朱玉笙婆家指望不上,无人撑腰也得指望朱维昌夫妇。
她左右为难,不敢离开。
朱玉笙的床被婶娘占领,只能立在窗前开门见山问道:“婶娘可是有事?”
贾氏也不好上来便抢侄女从婆家带回来的东西,夫妇俩商议过唯有让朱玉笙主动上交才是上策,于是便诉苦道:“玉笙啊,你自嫁进刺史府,不知家中今年茶叶歉收,家计艰难。”
朱玉笙假装听不懂她的言外之意,还嘲讽道:“婶娘这话我不爱听。茶叶歉或许是实情,但家计艰难料也不至于。不说别的,当初吴家给我的聘礼也不是一笔小数目,我在吴家帐房见过聘礼单子。就算咱们家所有铺面全都亏本,茶园田庄歉收,叔父扣留下的吴家聘礼也够全家舒舒服服吃好几年。”
徐氏见女儿不顾情面,连忙阻止:“笙儿——”
贾氏:“……”
哭穷这招不好使。
朱玉笙嘲讽反问:“难道我说错了?”
女儿言辞咄咄,徐氏招架不住,又忍不住哭了。
贾氏面上尴尬一闪而逝,见软的无用,又重整旗鼓大声斥责:“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你自十岁上丧父,你叔叔为了你不知道操了多少心,收点聘礼怎么了?值当你一说再说?”
她越说越觉得有理,声气渐粗:“你这丫头倒好,独个儿在刺史府吃香的喝辣的,被送回娘家之后不思感恩,连箱笼带房门都上了锁,这是防着谁呢?”
朱玉笙心中冷笑,面上却一副惊讶的模样:“防着谁?这后院住着不少人,院里的灶上的丫环婆子好些,人多口杂,万一哪个手脚不干净,少了东西我寻谁去。左不过婶娘同我没在一处住着,防不到你身上就是了。”
贾氏:“……”
贾氏被朱玉笙堵的哑口无言,暗骂这丫头去刺史府数月,回来竟变得牙尖嘴利。
她悄瞄了好几眼,刺史府里送出来的箱笼也是极好的,上面雕花刷漆,四角包铜,透着股富贵堂皇气息,让人心生羡慕。
可惜朱玉笙不为所动,打定了主意不肯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