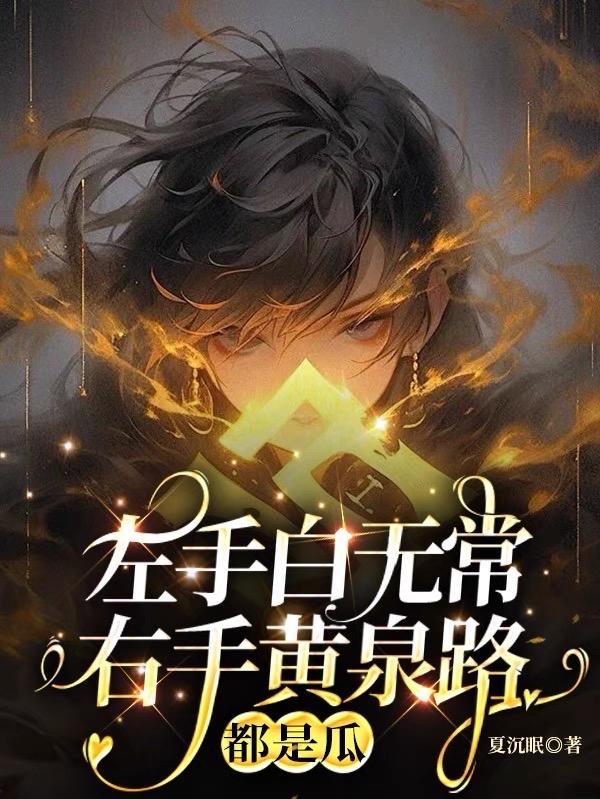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指缝间是什么意思 > 第26頁(第1页)
第26頁(第1页)
「所以你們可不可以先告訴我,你們所謂的想到了辦法,是什麼辦法?」
趙沅的父母對視一眼,最終還是由母親開口:
「今天上午,小亞細亞區域爆發武力衝突了。不是流民之間的小規模衝突,衛星拍攝到了重型武器。小亞細亞本來就有南華國和本州獨立國的實控區,這幾天國會也一直在喊話,要本州獨立國對邊禮欽的事情作交代。考慮到兩國之間的關係,這場在小亞西亞爆發的武力衝突很有可能是大型戰爭的開始……」
「等一下,」趙沅忍不住打斷了母親的話,聲帶開始有點控制不住地顫抖:「所以,你要去當戰地記者?」
「不是我,」母親微笑著糾正:「是我們。我跟你爸都會去。」
趙沅的喉嚨一下子哽住了,嘴唇顫抖著,半天才開始說話:「你們……你們幹嘛啊!不就是上個學的事兒嘛,至於你們做到這個份兒上嗎?我不同意,我不需要!」
趙沅越說聲音越失控,到最後已經有眼淚出來了,委屈又擔心地從眼角淌下來,又被趙沅伸手快地抹乾淨。
「我不管,」趙沅清了清嗓子,硬是梗著脖子說:「這錢你們給我我也不會用的,我不同意!」
父親見狀也有些傷感,伸手握住趙沅緊緊絞著的兩隻手,一字一句地說:
「阿沅,我們做這個決定也不是為了你上學,只是這個決定剛好能解決你上學的問題,你明白嗎?戰地記者是很有意義的職業,做的是很有意義的事情。以沒有偏向的視角講述事實,為難以發聲的人發聲,這是我和你媽媽一直想要做的事情啊。」
趙沅母親長出了口氣,也說:「阿沅,你也知道,外公外婆去世之後,我跟你爸爸的工作本來就有變動,從製作組到前方記者。與其被觀念不同的上級指揮,做非常淺表的調研,產出一些自己都不喜歡的內容;我跟你爸都覺得,倒還不如去做戰地記者,起碼是我們內心認可的事情。」
趙沅知道自己沒有辦法影響父母的決定,從小到大都是,父母從來沒有被他說服過。
趙沅仿佛已經看到了父母離開的場面,在飛機場大包小包地託運,笨重地回身朝他揮手。以及在電視機畫面里,穿著整套的身體防護,額前冒汗地講述現場情況……
趙沅忽然傷感起來,眼眶像是開了水閘一樣,開始源源不斷地流出眼淚來:
「但是……但是,那我怎麼辦啊……」
「我們阿沅,會長大的。」父親的眼眶也有些濕,捏著趙沅的手又加了些力,說話時語調也稍稍有了變化:「二十多歲的大孩子了,要慢慢學會變勇敢,變獨立,對吧?」
「哇」一聲,趙沅再也忍不住了,大喊著閉上眼睛哭了出來,把手抽出來緊緊抱住父親,把臉埋在父親肩膀上抽噎著哭。
母親見狀,也緩緩起身,站在父子二人身後,輕輕地摟住兩人地肩膀,還是忍不住默默流淚。
這個晚上結束得稀里糊塗。
趙沅最終也並沒有弄清楚他和邊禮銘之間的事情。不過,趙沅在今晚切身認識到了,他的自由是用多麼貴重的東西換來的。
某些人根本沒在意的,出生就有的,選擇的自由;原來對他而言,有著這樣沉重的代價。
因此也更不能被隨意地對待。
一家三口後來哭夠了,又開始聊天,聊了很多之前的事情。
趙沅記得自打他有記憶的時候開始,父母就在做那個深度調查欄目了,因此更驚訝為什麼這麼多年了,父母還會被從製作組「貶」到前方記者。
趙沅的母親說,可能正因為時間太長了,要堅守的東西太多了,執念太重了,才更不適應這個處處求變的聞時代。
趙沅的父親帶著追憶的微笑,幽幽地講起之前的在製作組裡的事情:
「一開始進組的時候,你媽媽就是製作組組長,節目組裡過一半的人都在攝影棚外做前方記者的工作。我第一個月也在做記者,後來整理出第一個案子,把聞稿交上去,就被你媽媽調來棚內做編劇了。後來我才知道,我那篇聞稿被她在整個攝製組傳閱了一圈。」
趙沅母親也笑起來,對上父親的眼睛,語間滿是溫柔:
「當時在看完你的稿子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找到了自己想要一輩子共事下去的人。」
第11章芳草萋萋
沿滄市向來不是個四季分明的城市。
春天和夏天的過渡非常模糊且反覆,氣溫總是隨著一場一場的雨上下變化;前一天穿長褲還冷,第二天或許就光著膀子都覺得熱了。
拖延拉扯之間,夏天總算分明地來了。
當上午十點出門就受不了太陽的熱度的時候,當就算下雨,濕熱的空氣也會從傘底翻湧進來直撲臉面的時候;趙沅和邊禮銘的本科生活,像一張即將燃盡的紙簽一樣,也漸漸只剩一個尾巴。
趙沅自那天起就沒再跟邊禮銘聯繫了,反之亦然。
趙沅有幾次路過大門緊閉的邊家院子,從低矮的院牆望進去,仍有一院的盎然綠意。趙沅好多次抬頭去看,那顆玉蘭樹露出了小半個鬱鬱蔥蔥的樹冠,油亮豐厚的葉片中,找不出一片白色的花瓣。
趙沅去學校走最後的畢業儀式的時候,路過了曾經一起和邊禮銘去的咖啡店。店還是做咖啡的,只是店裡換了軟裝,換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