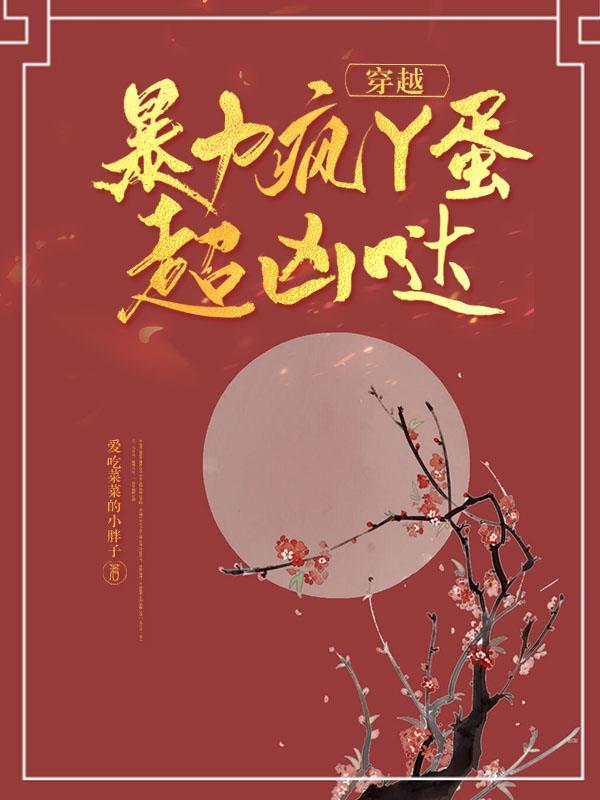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限速了会怎么样 > 第21页(第1页)
第21页(第1页)
那里的女厕没什么人,她在镜子前把头发撩起来,细细凝视那块淤伤,渐变的青紫色,像是烙在她额头的一小把烟花。
彭雪梅自虐式地伸手按了按,疼痛感仍旧新鲜,但跟昨晚相比已经好太多了。她把头发放下来,开水龙洗了手,边擦手纸边走出去,在门口碰到了张治年。
“你来了啊。”
张治年还是那副德行,温和地冲她打招呼,那份体恤毫无破绽,但彭雪梅还是敏锐地观察到,他的视线朝自己额头飞速地扫了一秒,又重归正常。
他越是什么都不表示,彭雪梅就越是反感,她挺直了腰板,冲他甜甜地露出微笑:“是啊,昨天家里有事,请了一天假。”
“是吗?”
张治年不动声色,他也不着急走,而是沉着地立在那,目光平静深沉,像是看破一切,又包容一切。
彭雪梅突然就产生了一种不该有的冲动,一股隐匿的破坏欲,逐渐从哪个角落里弥散出来,直至充满整个心房。
张治年要离开的时候,又被彭雪梅叫住了。
她朝他走近了一步,张治年一下就闻到了她身上那股刺鼻的香水味,嚣张又热烈,和乔小雯是两个极端。
他没有躲,脚下纹丝不动,看着彭雪梅美艳的五官近在眼前,她擦了口红的嘴唇轻启,对他发出一道邀请:“张老师,你晚上有空吗?陪我吃个饭吧。”
张治年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他沉着眉思考了几秒钟,问:“你有什么事?”
彭雪梅看出了他尚存的戒备心,觉得想笑。她点点头,主动把刘海撩起来,露出底下可怖的伤口。
张治年却不敢看了,惊慌失措地挪开了视线,彭雪梅从他这暂时的逃避当中,获得了一丝成功的满足感,她压低了声音,嗓音也变得黏糊糊的,从咽喉里慢慢挤压出来:“张老师,我需要你的帮忙。”
张治年罕见地落荒而逃,他都不记得自己最后答应了没有,总之反应过来时,人已经在办公室了。
室内开着空调,这台空调年纪大了,挡片泛黄,在高风速的震荡下微微晃动,发出噪音。张治年仍觉得燥热,他疑心这空调是不是坏了,一摸额头,一手的汗。
他强装镇定走到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处理没看完的文件,但密密麻麻的字符变成了蚂蚁,在雪白的纸张上毫无章法地爬动起来。张治年盯久了,甚至觉得手里的白纸就像彭雪梅的皮肤,依稀还能闻到她身上的香水味。
到了放学的点,张治年没急着走,反而是故意多留了一会。
手机就在手边,一条新消息也没有,张治年的手指就在桌面上一下一下点着,等了五分钟,终于屏幕亮了。
彭雪梅:张老师,你下班了吗?
张治年如释重负,不禁弯起嘴角,又心满意足地舒了口气,他把手机揣进兜里,拎着包出了办公室,走下楼梯时,彭雪梅正站在下面等他,见他来了,扭头冲他一笑。
两人一前一后出了学校,张治年径直去开车,而彭雪梅在离学校不远的公交车站台站着,车开过去时,远远地就能看见她。
她今天穿了一袭白色,长发飘飘,亭亭玉立,叫人没法不多看一眼。
张治年一度产生恶劣的想法,如果他就这么把车开过去,不停下,然后当今天的一切都不存在,彭雪梅是不是会被他气个半死?
这么想着,他不禁笑了出来,不过车最后还是缓缓在她面前停下了,彭雪梅拢了拢鬓角的头发,开了副驾的门,优雅地坐了进来。
她表现得从容淡定,根本不像是第一次坐他车的人,一边低头系好安全带,一边问:“我们去哪?”
张治年乐得配合她:“你想去哪?”
彭雪梅抿了抿嘴,她的口红仿佛是刚补过的,闪着鲜亮的光泽,她歪着脑袋故作天真:“都可以,不过还是去远一点的餐厅吧,你说呢?”
张治年懒懒地睨了她一眼,发现彭雪梅是真的在征求他的同意,她眼波流转,可怜巴巴地自下而上望着他。张治年心情一下就变好了,他看出来,现在处于优势地位的是他自己。
彭雪梅主动邀约,已经等于双手奉上了一个把柄,他接也可以,不接也可以,反正最后论起来,他又没什么过错,左不过就是同情心泛滥,太想帮助深陷痛苦的同事罢了。
“也好。”
张治年感到久违的轻松,他甚至觉得这才是正确的,先前他在乔小雯那里莫名其妙吃了闭门羹,挫伤了自尊心,现在急于从其他地方弥补回来。
他用余光瞄了眼身边的彭雪梅,她手无缚鸡,柔弱无力,没什么好怕的。张治年沉默地发动了车子,随着车轮滚滚向前,他内心甚至涌起一股好奇,不知道彭雪梅的空虚和他的贪婪比起来,到底哪一方会赢。
乔小雯对这一切暗流毫无察觉,事实上,她最近的心也根本不在学校。
陈嘉良音讯全无一个多礼拜,他像是铁了心要玩消失,不管乔小雯给他发什么,那头都沉默不语,甚至连朋友圈动态都没有。
乔小雯不禁怀疑,她是不是已经被拉黑了,尝试着转账了一块钱,结果钱顺利地发了出去,过了24小时又原封不动退了回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乔小雯相当乐观,只要还没删她,就是有希望的。
这就跟打游戏一样,高端的装备总是需要勇者披荆斩棘,越过重重难关才能获得,总不会就在路边随便能打开的小宝箱里。
乔小雯决定放弃死缠烂打的聊天战术,另辟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