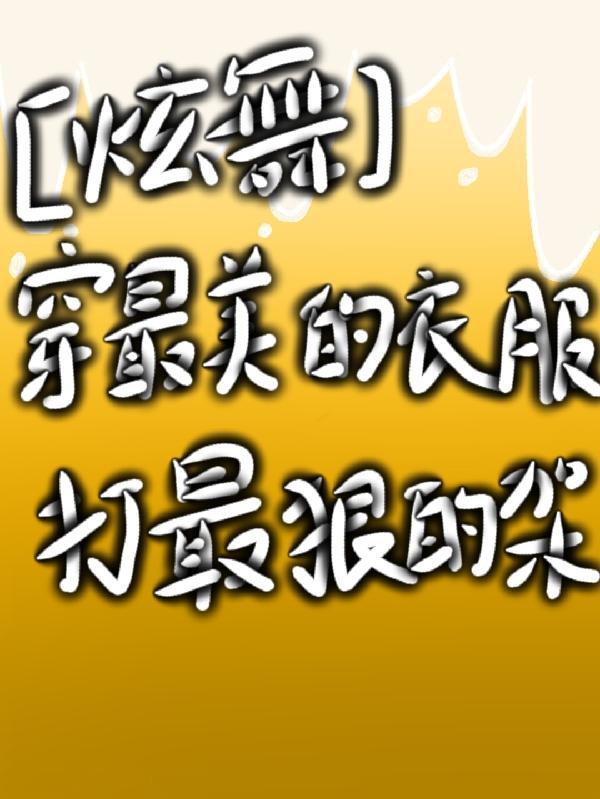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你是前世未止的心跳博肖 > 第37章 复仇下(第2页)
第37章 复仇下(第2页)
“不要这样叫我!”
谢危咬牙切齿道:“母已去,父不配,名成其辱,姓冠我恨,这样的名姓,我不要。这世上再无薛定非!”
“谢卿,朕自私冷血,且快油尽灯枯,死不足惜,母后残害忠良,亦是罪有应得,这两条命你们尽管拿去。只求你看在我们当年同穿一双虎头鞋的情分上,放过你的表侄——朕的儿子,善待除薛姝外的后宫妃嫔。”
沈琅言不由衷,他在赌谢危与燕临人性中的善有多少,他表现得越卑下、越善良、越为他人着想,他们可能就越犹豫,他还存着万分之一的希望,等沈芷衣来救他。
谢危咯咯笑起来:“沈琅,你还是那么会演戏啊,好,我就如你所说,拿走这两条命。别以为我会客气!”
“兄长,你似乎忘了一个人。”
燕临指着薛姝。
他曾做过一个梦,梦里他的宁宁被人按着趴在石架上,碗口粗的刑杖一下一下重重打在她极其娇弱的身子上,脸色如土,满头冷汗,依然倔强地咬着嘴唇不肯痛呼一声。
旁边站着一身宫装志得意满的薛姝,嘴角噙着冷笑。虽然是梦,他也恨得要死,这薛姝一看就蔫坏,在给公主伴读期间肯定没少欺负他的宁宁,宁宁肯定被这女人吓坏了。
谢危顺着燕临的目光看过去,不屑道:“只会爬床的东西,我懒得动手,你看着办吧。”
薛姝惊惧已极,为何都要她死?沈琅知道她下毒的事恨她可以理解,燕临怎么又记恨上她?
她大叫着求饶,什么谄媚的话都说了一遍,就差当众扒光自己献给人干了。
然而再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燕临将她提起使其趴在地上,亲自抡杖重重打了几下,他何等力气,一杖下去,薛姝几乎去了半条命,后面的无非是泄愤罢了。
很快薛姝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一双眼睛惊恐地瞪得极大。
兵士把死不瞑目的薛姝拖下去,至此,薛氏一族只剩薛太后还活着。
看着兄长侄子侄女一个个惨死在自己面前,薛太后心理防线彻底崩塌,鬓散乱、凤钗倾颓,全然不见往日的骄横跋扈之色,可她也不如薛远勇敢,只瑟瑟抖地等待着最后宣判。
“姑母啊,你曾对我母亲说,尊卑有别,贵贱不等,可你这样一个目无苍生满腔私欲狼心狗肺的东西怎配为尊?想要苟且偷生,就只能好好做我母亲的臣。”
谢危命人当众除去她太后衣饰,扯散头,换上囚服,押往燕敏墓前长跪。
沈琅咳出一口血,谢危终是将长剑对准他胸口,缓缓道:“君要臣死,你敢不去?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全仗圣上当年这八个字的激励。今日我为君,你为臣,我要你死!你敢不死?”
“谢危不可呀!你一身才华,乃国之柱石,切莫被仇恨迷失了心志,留下千古骂名。功臣与逆贼,就在你一念之间啊!”
顾春芳再次高呼,群臣也纷纷喊话哀求。
“住嘴!谁再多言,便同薛氏一个下场!”
谢危恶狠狠道,整个人散着凌厉的煞气,形同鬼魅,他猛地一动,一剑刺向沈琅。
沈琅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恍惚看见那个明媚活泼的少女笑盈盈向自己走来。
咣当一声,长剑脱手飞出,谢危大惊,蓦地看向燕临质问:“你!你为何护着他?你忘记血冠礼了吗?你忘了我们这几年是如何艰辛才重新掌控军队的吗?
就连你最宝贝的妻子,也曾被这个狗皇帝霸占过,你忍得了这种奇耻大辱?”
“兄长慎言,宁宁与我成亲时仍是完璧。”
谢危呆住,暗忖道,这怎么可能?沈琅有儿子,不是不行,怎么可能放过那个妖精一样的女人?这小子八成是要面子才这么说。
“燕临,我的好弟弟,只要你让我杀了这个狗皇帝,为兄便拥立你为新帝。”
谢危决定利诱,毕竟周边都是燕家军,绝大多数听命于燕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