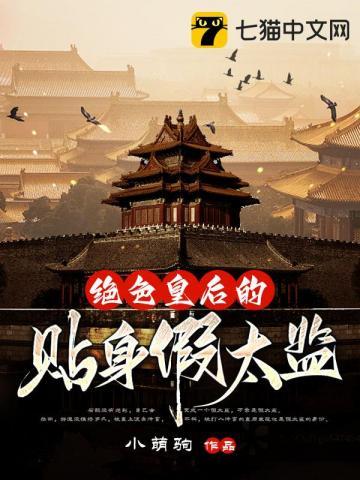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衣手遮天男主是重生的吗 > 第十一章 莫非他不是人(第1页)
第十一章 莫非他不是人(第1页)
谢景衣这一耍刀,便是一宿。
她伸了伸懒腰,看着眼前放着的整整齐齐的镂空雕花板和满地的碎屑,心中满满的都是满足之感。
这得赚多少钱啊!
上辈子她呕心沥血,做出来的锦衣华服,也不过是给那些宫中所谓的贵人炫耀争风罢了,多半是只穿一次便压箱底了。替旁人做嫁衣,哪里比得过自己暴富来得痛快?
屋子里颇为安静,青萍趴在一旁的小机子上打着瞌睡,头一点一点的,像是小鸡在啄米。炭盆里的火已经只剩下零星几点,微微的冒着热气。一旁的红泥小炉上烹着茶,微微作响。
谢景衣提了一件披风,悄悄的打开了门,一股子寒气扑面而来,让人精神一震。
她站在门口,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东方有些微微亮,今日应当是一个化雪天。
“该死,奴睡过去了。三娘子一宿没有睡,今日还要去徐通判府上的冰鱼会,这会儿还早,快先去眯一会吧。被子里的汤婆子奴一直在换,还热乎着呢。”
青萍听到了动响,急急忙忙的走了出来。
谢景衣点了点头,“这便去了。你叫你阿爹,今日上午,将屋子里刻的板,送到兴南街去,等我从徐通判府上回来,便去寻姚掌柜说夹缬的事。”
青萍忙不迭的点了点头,扶着谢景衣进屋。
“你不好奇,我何时学会了雕板?”
“小娘会刻玉板板,会雕墨板板,如今再刻个花板板有什么好稀奇的?昨儿个我还觉得稀奇,明明屋子里有一大堆刻刀呢,咱们怎地还要买”
,青萍说着,炫耀似的提起了腰间的一个玉章,这是她去岁生辰的时候,谢景衣送给她的。
谢景衣突然就笑了。
她年少之时,多半是附庸风雅,还没有成为大画师,就想着早早的准备好印章,到时候一章值万金……
“你说得没有错,都是板板。”
她说着,脚步轻快的迈进了门,朝着雕花大床扑去。
南地多湿气,被褥成日像是没有干似的,润润的,若是没有汤婆子,那整个人睡一夜都睡不暖和。
有青萍掐着时辰,谢景衣好歹没有误了冰鱼会。
小小的马车里,混合着四人身上的熏香气,让谢景衣有些脑仁疼。
“昨儿个你是捉鸡撵狗去了么?那黑乎乎的眼睛用粉都盖不住。”
翟氏说着,拍打了谢景衣一下。
谢景衣撅了噘嘴,今日徐家相看的是谢景娴又不是她,再说了嫁人哪里比赚钱更有意思。
“阿娘,你今儿给我大姐姐用了几斤香,我都要打喷嚏了。”
谢景衣说着,撩起了马车窗边的布帘子,只瞟了一眼,便立马关上了。
翟氏又拍了她一下,“做什么一惊一乍的,吓坏阿娘了。”
谢景衣扯了扯嘴角,“冷的。”
换你撩开帘子,看到一匹傻马,外加马上的弼马温,你不心惊?
说话间,那外头的马儿像是瞧见了熟人似的,愉快的嘶鸣了一声。
谢景衣的眼皮子跳了跳,不用探头,她都能够想到马上柴祐琛那张像是旁人欠了他黄金万两一般的脸。
临安城虽不小,但是官宦之家,大多数都是聚集在一块儿的,马车行不了多久,便到了徐通判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