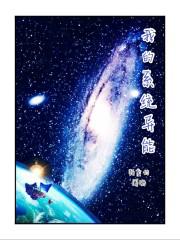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卿卿为君 > 第三十七章 崇王秦弘箸(第1页)
第三十七章 崇王秦弘箸(第1页)
该是有不可公之于众的部分。
“带王平远上堂来。”
他先把面子功夫做齐了,剩下的叫他们计较去,他才闲的清净。
“你方才也在下头听见了,你弟弟说的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倌龄把玩着案桌上的响木,时不时瞥他一眼。
“没有,他说的句句属实,卑职知法犯法,任凭大人处罚。”
“好个任凭处罚。”
秦北道:“王平远即日起撤去青州府衙师爷一职,罚银十两;伽迦大师,也就是王启远,数罪并罚,秋后问斩。”
不是要担罪吗?那便全部担好了,反正通奸之罪是他实实在在犯下的,如何也难逃一死,只是这谢家四姨娘吗,秦北闭了眼睛。
伽迦为她编了这样好的谎话,要保便保罢。
“退堂!”
伽迦一个头深深的叩在地上,府衙门外的人叽叽喳喳的散去,堂上的大人们也都离开,晓芸欣喜的站起来追着谢牧安走了。
连最后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
他跪了许久,没有人来扶他,只是眼前出现了一双蟠纹皂靴,他没抬头,但听那人说道:“谢谢你的谎言,泺梁百姓会同我一样感谢你的,还有什么事情想知道或者想要我去办的吗?”
“那件破屋里有三十两银子,劳烦你挖出来交给她,往后她在谢宅的日子不会好过的,得有个傍身的钱才能长长久久的活下去。”
“你好像很想她活下去?”
“你能听见我心中所想?”
那人没回他
,又问:“缚胎咒的事?”
“那是我的孩子,染着我的气息,所以谢牧安碰不得她。”
那人一点儿不惊讶,只是谢家四姨娘把孩子打掉的原因,除了四姨娘自己,应该没人能知道了。或许觉得孩子生下来是隐患,又或者缚胎咒本身就有问题,这个孩子的死去是伽蓝做的手脚,充当了计划的一个环节。
“活着对她来说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好事。”
“我知道。”
“这是爱呢,还是恨呢?”
“我不知道。”
那人似乎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了,衣角微动,那双蟠纹皂靴渐渐远去,伽迦却突然好奇起这人的身份。
“明月夫人,常氏无何。”
她果然能听见我心中所想,伽迦向着她离开的方向将头深深的叩了下去。
青州一案到此为止了,可这苦的要死的药什么时候喝到头啊?秦北看了一眼端着药碗进来的常嬴,都想把她推出去了。
药碗是只齿窑的杏花天影碗,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用齿窑的东西了。
“我不想喝。”
光说不算,伸手就要去推开。
常嬴一闪身便轻易躲开,顺势坐在他床边:“你上午审案子的气势去哪儿了?都不是小孩子了,忍一忍就过去了。”
反抗无效。秦北认命似的捻起那只碗,又是熟悉的味道,也还是熟悉的场景,果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我在汉云寺那尊大佛里发现了法文的痕迹,等我们回到锦城便修一条法令,禁止损坏
佛像,之后这样的事情便能少许多。”
她递上蜜饯,又道:“都是些神明使的法子,不过是图些尊敬,说出去人们未必会信,要是惹出非议便不好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神明自然要敬畏,只是没有被逼着去敬畏的道理。
“案宗文书收尾做完也就两天的时间,我们也该回锦城去了,明日便动身吧。”
秦北道:“西燕使臣昨天便离开了,你的病也称不了多少天了。”
也是,这就要五月了,又到了她找借口搜刮朝内文武百官家私的时间了。
回去的路上也就不那么着急了,毕竟秦北还伤着,车马一路颠簸,别说是他,就连常嬴有时候都适应不了。
况且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手边没有那么多的事儿要去操心,常嬴放慢了速度,权当是一番游山玩水,倒也乐得清静。
只是这清静很快便被打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