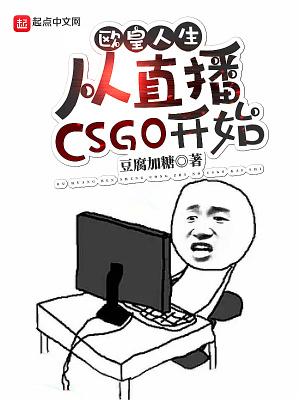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身为下贱 > 第44章(第2页)
第44章(第2页)
做完这一切,他才抬头去看池钺。
为了方便缝针,池钺额骨伤口周边的头被剃了一些,现在紧紧压着雪白的纱布,看起来没有流血。
他松了口气,小声问:“疼不疼?”
池钺注视着蒋序,看到他的眼神,低声回应:“不疼。”
夜里的输液室除了他们还有其他人,最前方的电视正在放晚间新闻,音量调到最小。两个人声音也压得很低。
蒋序忍了一路,还是忍不住问:“是你爸爸打的吗?”
他想,要是池钺不愿意回答,自己就找其他话题绕过去。没想到池钺只安静了两秒,随即点点头。
“他喝醉了,吵了两句。”
池钺说。
蒋序心脏像是在被人挤压,皱皱巴巴又酸得厉害。
“不要再回去了。”
蒋序声音带着一点恳求,“不要再让他打你。”
他垂头丧气的样子看起来比挂着点滴的池钺还要可怜。池钺忍不住用另一只手轻轻拨开蒋序额前有些凌乱的头。
“不会回去了。”
他承诺对方,“也不会再见他了。”
蒋序心情稍微好了点,努力对着池钺笑了一下。
“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
池钺摇摇头,他从早到晚都在路上,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但现在他并不是特别饿,只觉得累。
蒋序看出来了,池钺精神看起来不太好,脸色也有点白,于是又开口:“休息一会儿吧。”
池钺“嗯”
了一声,闭上眼睛。
蒋序打起精神盯着吊瓶,担心点滴空了自己没觉。
旁边的人头慢慢下沉,靠在了椅背上,梢隐约擦过蒋序的侧脸。
白色的墙壁,白色的灯光。吊瓶换了三瓶,蒋序看着输液管里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掉下来,像眼泪一样安静地流进池钺的血管。
等护士换上最后一瓶药水,蒋序估计了一下结束的时间,小心翼翼的起身。
他晚上没吃饭,原本想等着池钺一起过生日。现在已经饥肠辘辘,又觉得池钺醒了可能也会饿,飞快跑出医院想买点吃的。
大年初三的深夜,医院外开门的店寥寥无几,大多都是便利店。蒋序不敢走太远,又谨遵医嘱不想让池钺吃食,最后找到了一家快要关门的粥店。
店面很小,门半关着,老板已经收起了所有的凳子在拖地。蒋序探进头轻声问:“还有吃的吗?”
店里最后剩的是生滚猪肝粥,蒋序想起猪肝好像补血,点了两碗拎回医院。
池钺还没醒,吊瓶里药还剩三分之一。他把一份粥扎紧袋子,用自己的外套盖好,把另一份打开。
动物肝脏独有的味道混在粥的热气里,蒋序舀了一勺放进嘴里,那个味道让他有点反胃,第一口差点直接吐了出来。
但是现在已经快要到凌晨,他也真的很饿。
最后,蒋序压着胃里不由自主泛起的恶心,低着头一勺一勺把那份猪肝粥吃干净了。
等他吃完,池钺的吊瓶终于全部低完,他去叫了护士拔针,回来又把池钺轻轻摇醒。
见池钺睁开眼,蒋序把旁边位置上的外衣拿起来穿上,摸摸粥碗,还是温热的。
他打开递给池钺。
池钺拔完针,低头安静的喝粥。忽然没头没尾冒出来一句:“今早在高铁上,我还在想你喜欢吃什么,晚上可以带你去哪儿吃饭。”
蒋序从愣怔中回神,电视里深夜新闻告一段落,刚好开始自动报时,差十秒钟到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