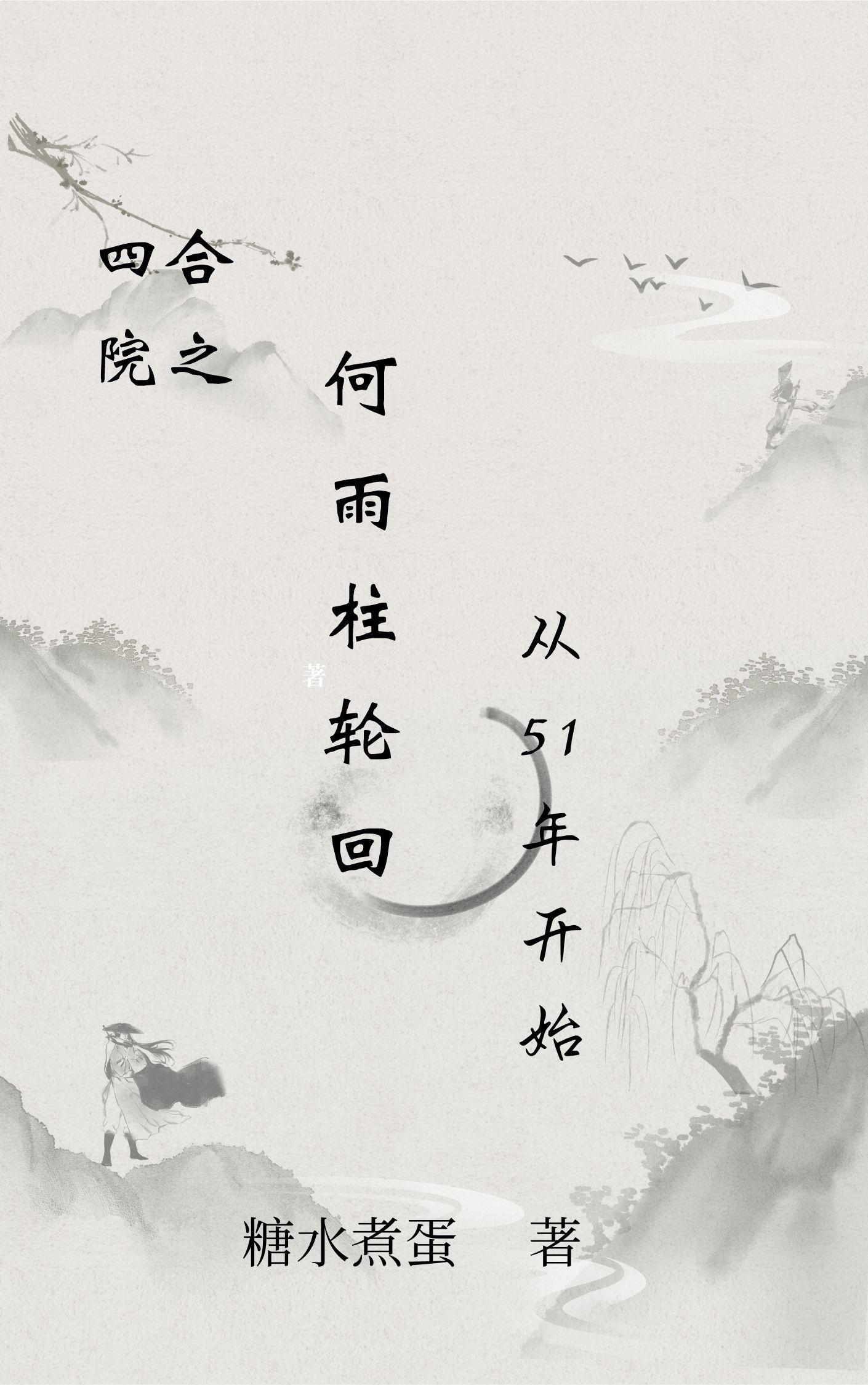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情人谷的传说 > 第5頁(第1页)
第5頁(第1页)
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聞家所有人都暗懷鬼胎,為控股權爭的頭破血流。
聞鈺是個從來沒有入過局的人,失去掌權人的庇護,先被當了祭品推出去,二十歲的年紀,聞書然白事未盡,她自己的紅事已定。
葬禮上她淚流滿面,面前的人和物都模糊不清,她像爛泥狼狽不堪的暈倒,沒有預料中的疼痛,她栽進一個陌生男人的懷裡,好像有點浪漫色彩,但卻不是任何童話故事的開始,她連結婚對象的名字都還不知道,像個機器人服從既定的流程。
婚後聞鈺完全避世,變成啞巴。裴硯青也不管她,只要她不去尋死。
想活下去必須得找些事轉移注意力,於是她開始整日躲在書房裡抄墓誌,男男女女的,最後是夫妻的。
她發現南宋很盛行「夫妻合葬」墓,左右排列的長方形墓室,略有高下錯落,左室較右室稍高,證明「夫為妻綱」。
墓誌不談論愛情,因為崇尚「相敬如賓」。
大談丈夫的功德,最後末了,才潦草提及「娶某氏」云云,對於繁衍的子女,描述的筆墨就更詳細。
聞鈺的愛情觀是從墓誌里慢慢形成的。
裴硯青平常大多時候克制,偶爾也會吻她,聞鈺不會拒絕,也不會回應。
同床共枕當然有過,可她習慣了一個人睡,所以在裴硯青身邊會失眠,然而都沒等到她開口,裴硯青已經不強求了。
總之雖然是夫妻關係,但親密的瞬間都很少很少,大多時候,聞鈺安安靜靜的翻書,裴硯青想陪她,就在一邊處理公務,互不打擾。
後來不記得是哪次宴席,因為聞鈺沒戴婚戒,有個外國男人以為她是裴硯青的情人,特別輕挑的用英語問:「你睡過她了嗎?」
當場所有人都震驚了,沒人敢再笑,也沒人敢吱聲。
裴硯青通常不會做讓自己沒有退路的事,他習慣了衡量得失,讓利益最大化,何況眼前這個外國人是裴氏的重要合作對象,關係破裂只會影響股價。
但他確實是有點失控,額角的青筋都蹦出來,咬著牙對旁邊的陳才說了兩個字:「清場。」
聞鈺其實對於言語的冒犯並沒有太大的反應,她不太在乎別人用這種事來攻擊她,因為她覺得不重要。
估計是場面血腥,裴硯青沒讓她看,她就站在門外,聽裡面不斷的撞擊聲和哀嚎,二十分鐘之後她被帶進去。
「他要跟你道歉。」
裴硯青氣息還不穩。
他臉上濺了血,右手骨節處破了皮,拽著那個男人的後領,粗暴地把他從地上拖起。
聞鈺對那人怎麼道歉的印象不深,但記住了那時候滿身戾氣的裴硯青。
訴諸暴力肯定要承擔後果,那段時間裴氏受人故意抹黑,風評極差,聞鈺雖然平時兩耳不聞窗外事,但也上網,她覺得自己給他添了麻煩,於是把那枚婚戒翻出來戴上。
裴硯青很快發現她無名指上的變化。
有點受寵若驚的意思,但裝作冷靜,問她原因,聞鈺沒有說點情話討人歡心的自覺,她老老實實的,話有點殘忍:「規避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