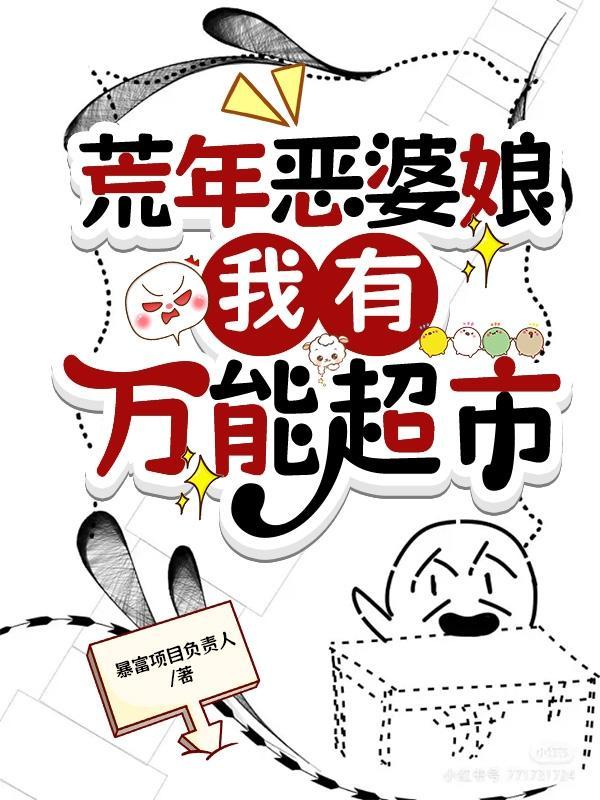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古典制约情节梗概 > 第63章(第1页)
第63章(第1页)
牧长觉会看出来。
然后他点头。
“那你现在是去见他吗?”
牧长觉问真心话不再需要赢。
燕知又点头。
“他是最近联系你的?”
牧长觉继续问。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确切。
但燕知还是点头。
漫长的沉默。
“那我就不陪你去了。”
牧长觉的声音仍然很轻,轻得燕知觉得嘴里太苦了。
好像他这辈子吃过所有的药此时此刻都通过喉咙返上来,只要他一张嘴就会全吐出来。
“燕知,我没有怪你,我永远也不会因为任何事指责你。”
牧长觉的声音里有很淡的疲倦,“其实和你猜的一样,我知道了你走那天的一些情况。包括从前、现在和以后,你做出任何的选择我都会理解,并且尊重。尤其在当时那种情形下,我宁可你有人陪着。”
他抬头看着燕知,“错从来不在你。”
他的声音太轻了,如果不是如此清晰的内容,燕知简直分不清究竟是不是他说的。
“只要能让那时的你感觉好一点,我很希望有人可以弥补我的缺席。”
“少喝点儿。”
牧长觉走的时候拿走了桌子上没开的酒,留下了自己的外套,“另外替我谢谢他。”
时间晚了,小店里的学生越来越多,逐渐热闹起来。
燕知能听见老板在挨个查学生的身份证,“没成年的同学不许喝酒啊……差一天不行!差一个小时都不行!”
燕知想起来那部从小时候就喜欢的电影,说差一个时辰都不算是说好的一辈子。
一辈子多奢侈啊。
看电影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懂了,结果还是许了要跟牧长觉一辈子在一起的愿望。
燕知不知道这一次他有没有做到一个好的告别。
他想自己会想方设法地回来。
但是如果他没找到办法,那他也很难想象如何让牧长觉目睹那个支离破碎的自己。
他想给牧长觉一个恰到好处的伤害。
如果他不能以完整的自我回来,那牧长觉最好可以觉得自己没有他也可以过好的生活。
就像他无论是不是自内心地说过的那样:有人弥补他的缺席。
至少他们当中有一方不那么遗憾。
燕知以为这会是很难的。
他看着牧长觉从头到尾没有碰过一口的酒,莫名有一种破釜沉舟的轻松感。
酒精混着最空虚的如愿以偿,他对着空气笑了,“你听到了吗?他叫我‘燕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