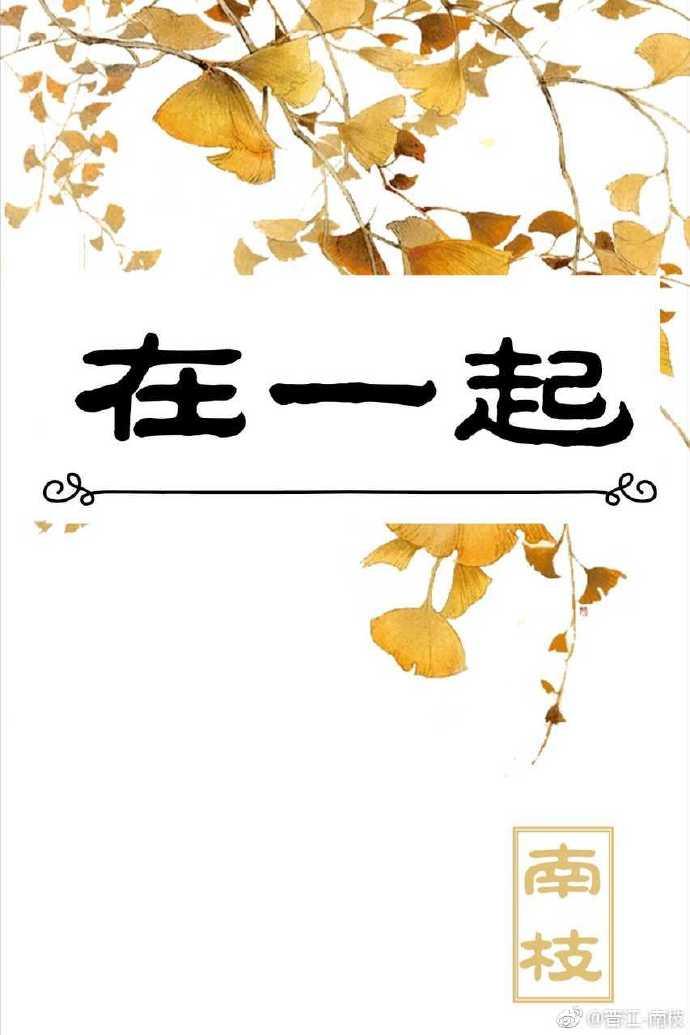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贵妃娘娘千秋免费阅读全文 > 第47节(第1页)
第47节(第1页)
这一晚。分明同被而眠。二人却楚河汉界互不搅扰。什么都有发生。
若抛去孟绪不算好看的脸色。倒也勉强称得上相敬如宾。
一直到第二天。鸡鸣际分才过。孟绪摸着黑就起来了。亲自下厨炖了鸡丝粥。自己用了一碗后。又吩咐宫人将剩下的粥在灶上热着。“不必惊动陛下。等他醒了。再问他要不要尝尝就是。”
而后径自离去。
就好像她之所以还肯留在太极殿。不过是因为同他说好了要用过第二天的早膳再走——
帝王在等她落泪。
他有他的无情大局。而成事必要有所牺牲。因而不惜将她置于险地。只等她自己想通。
而她也在等。等他先忍不住。忍不住低头来哄。
难过自是假的。要人愧疚、要人心疼才是真的。
这一次。就看谁。先为谁落泪。
*
肩舆是一早就抬了回去的。徒步走在回程的路上。簌簌见主子和陛下闹得这般僵。一面发愁。一面又对樊氏的事唏嘘不已:“同一屋檐下这么久。咱们竟也有发现。所以。她既不是商女。也不是瘦马。都是幌子?”
孟绪点头:“用两重身份混淆视听。反教人拘泥于这两重身份。一叶障目了。”
就像她一早就发现了樊氏与大梁这一代的闺秀都不同。足不盈三寸、小若玉梭。却只以为是她瘦马出身的原因。
瘦马本为取悦权贵而存在。一双莲足也常常沦为供人娱笑之物。
她又一贯不想樊氏因出身难堪。便也不曾提起。
这才忽略了。女子裹足亦为雍朝的陋俗。
“万幸的是她有真的对主子下手。”
簌簌感叹。“其实奴婢头先就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人。可那回她帮主子识破了那毒。奴婢便以为是冤枉了她了。怎么都有想到她竟是这般包藏歹心之人。”
簌簌对樊氏的看法一波三转。孟绪有过多解释。只说了句:“人哪有非黑即白的?”
就连帝王也不算什么完人。
于国于朝。他的做法固然无错。
他早知樊氏来者不善。却还是让人顺利进了宫。想必就是想利用樊氏钓出更多蛰藏在宫中、为雍朝效命之人。
她固然是那颗钓樊氏子棋。樊氏又何尝不是帝王运筹帷幄之际的掌中棋子?
可作为一个女子的夫君。他的心却委实有些狠了。
难道定国除叛。必定要以一个小小女子都牺牲为代价?
不过孟绪对此并不伤心气恼。
更不会因此与帝王有什么嫌隙、芥蒂。
甚至这样的帝王心术。反而很合她的心意。
可她却需要让那位多疑的帝王以为她会为此伤怀。也要让他相信。纵然伤怀。此事却断不会在日后成为隔阂在他与她之间的芥蒂。
所以。她才选择了先主动让这件事成为芥蒂。等来日。再让他亲眼看着她放下——
她与他。本就是互相下计。又有什么好气?
这些事却不必告诉樊氏。
簌簌还自在那儿放不下樊氏的事。
因今早簌簌是跟着空的车舆先回了月下阁的。樊氏行刺的际候她并不在场。具体事况也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
“不管怎么样。主子也帮了她不少。骂主子就是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