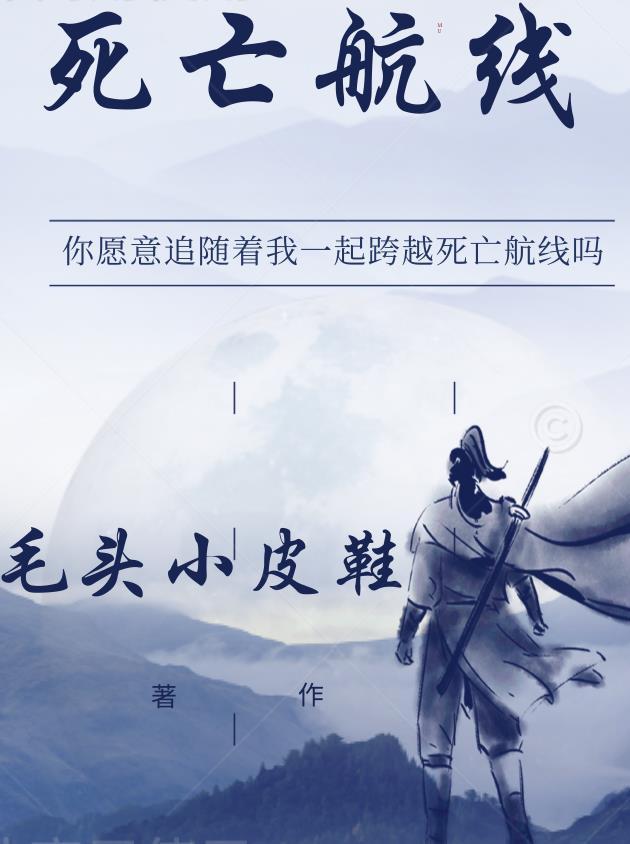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黑莲花女主古言 > 第3章 开堂刨尸(第2页)
第3章 开堂刨尸(第2页)
他低咳了几声,声音似乎比平日里更加低沉沙哑。
知府点头,徐仵作不再耽误,将盖着陈尸的白布掀开,“王大”
的脸被火烧的面目全非,整个身体白浮肿,表面坑坑洼洼,依稀能看到炭黑皮肤下的红色肿泡,两个漆黑的眼孔大睁着,空洞又恐怖。
“大人……还是回避一下吧。”
徐仵作回头对着站在一旁,已经脸色白的青衣讼师道。
讼师勉强说:“不……不打紧。”
“这位小娘子……”
徐仵作又犹豫的看了一眼立在一侧的冯葭。
冯葭熟练的将姜、醋倒在一方白巾上,捂住口鼻,只道:“若这具尸体真是王大,他养我十三年,已如家人,我自然不怕,若不是王大,那便与这凶手脱不了关联,既是仇人我更不怕。徐仵作只管验尸即可。”
徐仵作便不再作答,手腕用力,走刀不徐不疾。
“王大”
的尸体从喉咙处割开,鲜黄的油脂沿着行刀刀轨迹一股股的冒出来。
讼师只觉肠胃翻涌,转身奔走,扶墙哇一声吐了出来。
围观百姓中也隐隐传开干呕声。
徐仵作手里没停,刀如龙蛇游走,一气呵成,但还是寻隙微微侧目,撇了身后人一眼。
女子约莫十三四岁,穿着一身破旧的布衣,桃木钗子斜斜插在髻,衬的她脸庞消瘦憔悴。五官明朗清致,琉璃般的杏眼上偏生了一双英气十足的眉,腰身很细,身段窈窕,像是三月春风里摇曳的柳条,柔软却坚韧。
她的眼睛紧盯着尸体,脸上从始至终都无半分不适。
半柱香后,徐仵作收刀,跪于堂中。
“徐老,如何啊?”
“回知府相公……咳咳……死者为男性,按照骨缝推断年纪应在五十上下。喉咙处呈现深褐色,但肠胃里却无毒药残留,后脑勺有碗状伤口,考虑是被钝器砸击后脑致死,死后被人灌毒。死亡时间应是三月十四,也就是前天夜里到昨天白天。右肺熏黑,异于常人,因常年与油烟相伴。双脚长度有明显差距,是个跛子。”
“不是毒?竟然是被人死后灌毒?可其他三人都是毒身亡啊……”
“五十上下……还是个跛子?”
“那这尸体真不是王大呀!王大正是三十壮年,而且这徐老也说了,此人与油烟相伴,这王大是个猎户啊,跛子更无从谈起啊!”
真是咄咄怪事,这好端端王大的尸体变成另一个人?还是死后灌毒?是要掩盖什么?此人又是谁?与凶犯有何联系?为何死后会被水浸泡过?真正的王大去了哪里?是死是活?知府揉了揉涨的双眼,茫茫然然。
又现一大疑点:“徐老,你说这具尸体的死亡时间是在前天夜里到昨天白天?可是先前衙门仵作怎么验出的是今日晌午?这其中竟有一日之差?”
徐仵作道:“回禀知府相公,这具尸体白浮肿,两眼凸起,应是死后被冻在冰水里一夜,温度原因导致尸斑形成缓慢,衙门仵作才错认死亡时间。”
堂中一片沉静。
众人俱陷在此案的扑朔迷离之中,理不出个思绪。
“若没有其他事情,咳咳……老夫就先行告退了。”
徐仵作背起木箱,冲着知府拜了拜,随后拖着一条残腿先行离开了。他佝偻的身影没出衙门府多远,只觉得有道目光从他离开时便一直追随着他,不由微微转目。
那个像柳条一般纤细的少女。
她立于堂中,午后的阳光照得她一身通透,无瑕无垢,目光幽深如潭水,此刻正紧紧盯着他。
徐仵作收回目光,似浑不在意,深一脚浅一脚的走远了。从衙门口走到西街,那佝偻的身躯最终进了街口弯处便再没了踪影,不多时,一身暗紫色锦服,头戴纱冠的年轻少年走了出来。
他紧抿着薄唇,气质淡漠脱,不似凡尘俗物之人。遥遥看了那府衙的方向,眼神冷冽似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