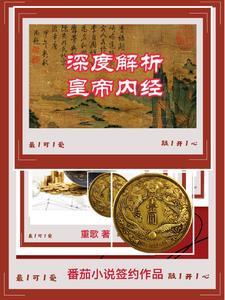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蔷薇庄园防空怎么放 > 第73章 羽泠小姐(第1页)
第73章 羽泠小姐(第1页)
回程的路上很安静,沈嘉念脱了鞋蜷缩在宽大的座椅里。
脚踝处隐隐作痛,身体和心脏疲累不堪,那些七零八落的情绪也如潮水般退去,整个人昏昏欲睡,脑袋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
车程不长,到了蔷薇庄园,沈嘉念没让傅寄忱抱,自己穿上拖鞋下车。
医院开了一瓶碘伏,让她在伤口愈合前一天涂两到三遍,她拎着小袋子上楼回房,先去卫生间洗澡。
“嘉念,我进来了。”
门外是周容珍的声音。
沈嘉念刚洗完澡吹干了头,闻言应了一声。
门被推开,周容珍端着吃的进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鸭汤,一份生煎,上面洒着碧绿葱花和白芝麻,旁边一个小碟子里装了蘸料,醋味又香又浓。
“先生让我来给你送宵夜。”
周容珍找地方放下手里的托盘,暂时没走。
沈嘉念晚上在饭局上吃了些东西,肚子不饿,但她不想浪费珍姨的心意,点头说:“我等会儿吃。”
她拧开碘伏的盖子,捏着棉签蘸取,涂抹在伤口处,没被吸收的深褐色药水往下淌,脚下的沙即将遭殃。
沈嘉念手忙脚乱,幸好周容珍及时递来一张纸巾,她擦了擦快要淌到脚底板的液体,才让昂贵的沙幸免于难。
周容珍拿来垃圾桶,方便她扔东西,很突兀地开口说:“先生还是在意你的。”
沈嘉念抬起一双干净的眼,看着她没说话。
周容珍说:“你转身离开的时候,先生站在落地窗前抽了好几支烟,心情特别差。”
沈嘉念不怕她笑话,自嘲道:“可能对他来说,我更像是他的私人物品,他只是不喜欢有人惦记他的东西。”
“嘉念你怎么会这么想。”
周容珍不可思议道。
沈嘉念摇摇头,没解释那么多。
有些事珍姨不清楚,她自己心如明镜。
周容珍自知说出那两句话已是不合规矩,当佣人的第一条准则就是少说多做,她笑笑转移话题:“你吃完了放着别管,我明早过来收拾。早点睡觉。”
“嗯。”
沈嘉念懂珍姨的用意,她既是关心她,也是为傅寄忱好,“谢谢珍姨,您也早点休息。”
房间里只剩她一个人,她绑起头,坐在桌前吃宵夜。
一盘生煎吃了三个,一碗汤喝了一小半,实在吃不下了,沈嘉念托着腮目光呆滞。
外面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咚咚”
两下。
沈嘉念放下筷子过去开门,已经猜到来人是谁。
傅寄忱洗过澡,换了身浅灰色质地柔软的居家服站在外面,头微湿,眼眸幽邃,让人联想到不见天日的原始雨林。
两人从医院里出来就没说过话,不存在和好,好像也没有太激烈的矛盾。
沈嘉念一手扶着门把,错开身让他进来。
傅寄忱鼻端微微耸动,闻到了食物的味道:“吃的什么?”
“不是你让珍姨送来的宵夜吗?”
沈嘉念顺手关了门,跟在他身后,“难道珍姨是骗我的?”
傅寄忱:“是我让她送的。”
“哦。”
沈嘉念点了下头,指指桌子上剩了一大半的宵夜,随便问他,“你吃吗?我吃不下了。”
傅寄忱停了脚步回头,一副“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
的表情看着她。沈嘉念在他意味深长的眼神里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居然让傅大吃她剩的东西,她也是胆大包天。
“我开玩笑的。”
沈嘉念讪笑一声。
傅寄忱视线下移,扫了眼她瘦骨伶仃的脚踝:“伤口还疼吗?”
“涂过药,好多了。”
沈嘉念拆下圈,一头乌黑的丝松散下来,披在身前背后。因为刚吹干就扎起来的缘故,丝留有圈绑束过的痕迹,微微蜷曲,有点像烫过大波浪,海藻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