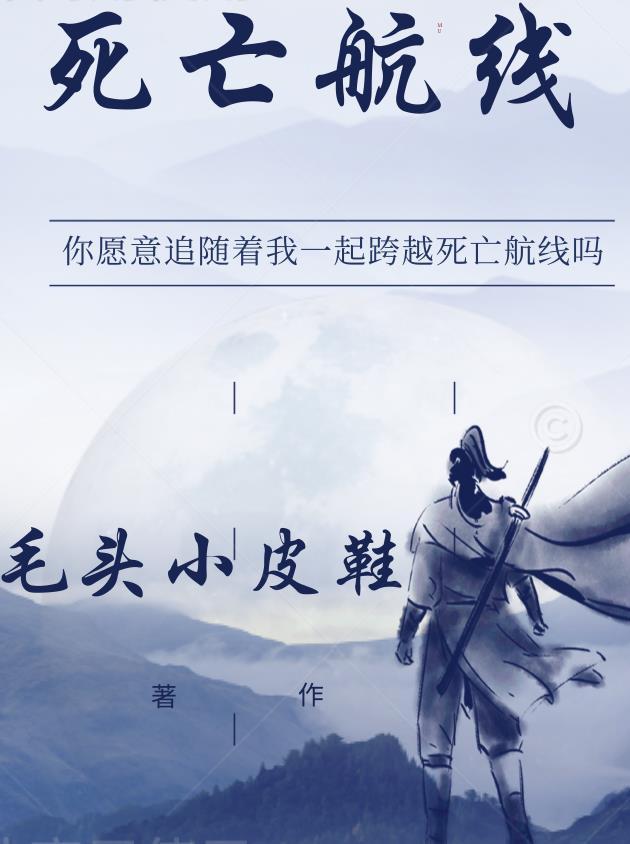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少女龙王终于收到男祭品 曲池 > 第67章 无定寺-凫山(第2页)
第67章 无定寺-凫山(第2页)
这些日子以来,黎川总是这样,总有那么一阵儿,她不似她,迷离,纠结,痛苦且深刻。
有时是梦中醒来,有时是恍惚昏去。
可等她醒来,又好似什么也没生。
整个京都都在传言,曾经“一箭定军心”
的云阳先生,一度艳压群芳的准镇北王妃,如今成了一个疯子。
“除了黯魂汤,圣上究竟还对她做了什么?”
萧洵安靠在椅子里,直直盯着桌案那头的文帝。
文帝举着一本折子看着,言道,“那玉枕是个老物件儿,后宫里出来的。锋芒太露的女子,在后宫待不下去。”
萧洵安伸手从文帝手中将折子抽出来,顺手丢进了笔洗里,“你的后宫如何,我不想知道,但我的王妃,由不得他人伸手。”
殿内没有其他人,文帝看了一眼那本泡进污水里的折子,抬头接住了萧洵安的眼神,“你父王就是娶了心思太重的女子,才落得那副下场,朕不会害你。”
看来文帝这里,也并没有其他的线索。
萧洵安当即站起身来,未作告退,直接拂袖而去。
襄妩宫经年紧闭的大门被推开了,萧洵安在门口吐纳一口,跨过门槛走了进去。
殿内无火盆,也未烧火道。整个宫殿好似北宫一般清冷,静谧。
一步一步走进去,反光的青砖,像是塞北雪林中的黑水,漆黑,冷冽。
良妃跪在蒲团上,面前是一幅幅面很宽大的山水长卷,那是涵王亲手描绘的江山美景。
即使听到有人进来,也并没有睁开眼睛,而是继续跪坐着。
似乎来者并不是她多年未见的亲生儿子,而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宫人。
萧洵安站在她身后,终于还是唤了一声,“母亲。”
不是母妃,没有任何其他的身份,只有他们之间,最直接的纽带,母子。
良妃睁开眼来,却没有回头,她只是看着面前的山水,“为了她,你才来找我。”
萧洵安心中似乎堵着一块湿重的陶土,想要冲碎它,它却绵软地缩回去,而后又以另一种形态继续拥堵。
他可以对任何人嗤之以鼻,嚣张无礼。
可面前的,是他的母亲。面对母亲,无论她怎样,他永远是谦卑的,是讨好的。
“你觉得,我对她做了什么,来兴师问罪了。”
良妃并不是问,而是缓缓称述了出来。
“不是的……”
萧洵安垂手立在那儿,他其实是想来问问良妃,是否清楚黎川的情况,毕竟她是调香制毒的高手。
可他又怎么问得出口,这好像是在提醒自己的母亲,是她用最恶劣的谎言,最恶毒的毒药,害死了他们的父亲。
“你想要权柄,就不该耽于男女私情。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个女子。”
良妃站起身来,转过头,看向萧洵安。
而后,又回过头去,闭上眼睛,“你知道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永远忠诚,特别是你以为可以交付终生的人。”
言罢,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这叹息似是对旧事的悔恨,又似对萧洵安的失望。
风雪摇摇,宫道杳杳。
萧洵安像一缕孤魂,飘荡在这人世间。
“王妃不是得了痴症。”
一个声音将萧洵安从空荡荡的遐思中拖出来,此时才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宫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