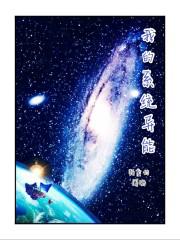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那个漂亮钓系是我老婆 > 第31頁(第2页)
第31頁(第2页)
偏走的話題,又被他給拐了回來。
「或者說,我覺得,沒有人能配得上你。」他的語氣認真,眸色間也透著真切,像是在陳述一件既定事實。
軟椅上的男人正襟危坐,雙手搭在膝蓋上,聞聲,手指不由擠壓著自己的大腿,仿佛要將腿上的布料壓出印子來。
「對於你的擇偶問題,我也持同樣態度。你病了,沈焉有來關心過你嗎?」
他知道這種在背後捅刀的事情不光彩,但他還是這樣做了。
並非全然出於嫉妒心在作祟,更多的是他實在放心不下溫硯和這樣一個不靠譜的混蛋在一起。
「他……應該還不知道我生病了。」溫硯垂眸,一副替沈焉開脫的神情。
季知遠見他這副樣子,渾身血液都開始往頭頂沖,坐不住了。
他起身,彎下腰來給溫硯掖好被子:「你再休息會吧,我就不……」打擾你了。
話音未落,抓著被角的手便被輕輕拉住,不讓他走。
是溫硯。
他將被下的手伸出一截,牽住他:「剛剛我不知道是不是做夢,夢見季大哥握著我的手,一下就覺得很心安。」
那確實不是夢。
是季知遠見他昏昏沉沉的,像易碎品一般叫他心疼不已。
所以忍不住在床沿握著他的手握了好長時間。
「所以,季大哥能不能別走,等我睡著了……再離開。」溫硯抬眸望著盡在咫尺的男人。
彼時的季知遠是俯著身的,那張臉正對著平躺的溫硯,男人頎長健碩的身影遮在他的眼前。
溫硯的眼直勾勾的盯著他,語氣又是那麼的單純。
似乎溫硯全然沒有要營造曖昧氣氛的意思,容他一個人墮進沉沒。
他的耳根莫名開始發燙,喉嚨開始變得乾涸。
他莫名想要譴責自己,譴責自己的道德敗壞。
「好……我不走。」他僵著手臂,不敢對上溫硯的眼,重坐回軟椅上。
溫硯的手掌微涼,掌心的肉軟乎乎的,裹著他的手指,很舒服。
他安靜的坐在床沿,溫硯則安心的垂下眼,漸漸的又迷糊起來。
伴著窗外有淅淅瀝瀝的雨聲,溫硯再次墜入夢鄉。
他一直昏昏沉沉,直到窗外的雨天放晴。
那已經是兩天後的事了。
季知遠這兩天一直在無微不至的照顧著他,直到溫硯的病情逐步好轉後才安心的回學校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