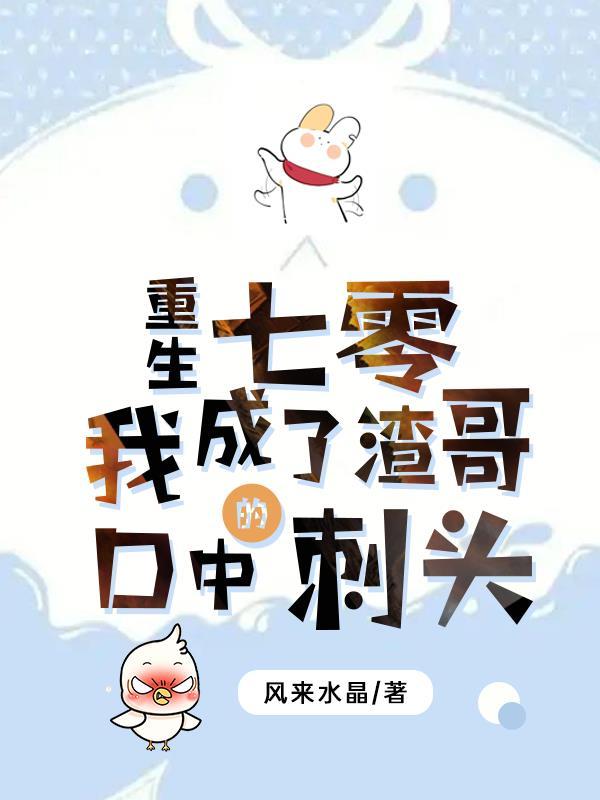完美小说网>为什麼要奖励他人 > 第36頁(第2页)
第36頁(第2页)
季唯洲蔫頭巴腦,他是真覺得這個任務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
他拿出手機翻學習資料,找合適的台詞,越看越覺得這些東西不適合在這個場合說。
青天白日講這些話,不合適。
季唯洲學來學去,最後還是收起了手機。他對江淮雪說的話,就是兩個方面。
虛擬的缺點,真實的困境。
「江淮雪。」他喊住江淮雪,走到他身邊,垂眸看向他冷淡的臉。
江淮雪看著季唯洲那個神態,沒什麼難度就猜出來他要幹什麼。
「跟我過來吧。」他對季唯洲說。
輪椅進入室內電梯,季唯洲和他去了別墅二樓,走廊最深處的房間。
上鎖的房門被打開那一刻,季唯洲的記憶似乎也跟著亮了亮。
他總算想起來在那本《禁庭之春》的江淮雪番外里,這個房間是什麼地方了。
這裡是江淮雪的刑堂。
前夫哥最後就是在這裡被折磨一通,丟出別墅,最後走投無路慘死的。
整個房間都是陰沉的黑色。深黑色的地毯鋪滿了房間,所有的血跡會被輕而易舉掩蓋。
季唯洲看著滿牆五花八門的刑具,打了個寒戰。
他站在房間門口,就察覺到冷風從里冒出來,直直往他身上灌。
但他又清楚這個時間點,這個房間還沒有見過血。
「你在害怕?」江淮雪語氣淡淡,連看都沒有看他,自顧自推著輪椅進入房間。
季唯洲矢口否認:「沒有。只是比較震撼而已。」
正常人看到這滿牆的刑具都得愣一愣吧?
季唯洲想了想,還是很誠懇對江淮雪說:「我尊重每個人的喜好。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我的包容心還是很強的。」
江淮雪平靜戳穿他鎮定的假象:「你的手在抖。」
季唯洲把兩隻手背到身後,再次否認:「你看錯了。」
江淮雪的輪椅碾過柔軟的地毯,只有細碎的聲響,季唯洲每次聽著江淮雪發出的動靜,就容易幻視一條蛇生活在這幢別墅里。
他略過那些皮拍刀具,最後停留在鞭子前。
「季唯洲,你不是想要折磨我麼?」他轉過頭,深黑色的眼眸一眨不眨盯著季唯洲。
他那一瞬的眼神稱得上平靜,並沒有多少波動,但季唯洲與他對視的那一刻頭皮發麻,如臨深淵。
這種感覺他說不上來,有點難受。